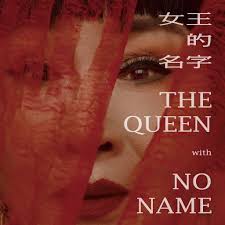 |
臺灣京劇表演藝術家魏海敏,自1991年問藝於梅派以來,除傳承本門經典劇目,亦積極嘗試和不同派別、其他藝術領域共同創作,努力開展表演新氣象。
魏海敏所演新編戲,無論是否為戲曲,因其參演緣故,女性角色會佔相當份量,且劇本和人物常跨越傳統規範。本文舉其兩齣「女戲」——幾年前的《孟小冬》(下稱《孟》)與今年的《女王的名字》(下稱《女》),分別以民國時期京劇名伶孟小冬和清朝慈禧太后為要角的劇作,從中了解當代人如何詮釋歷史、人物與敘事手法。
《孟》敘述民國京劇坤生孟小冬,年輕即享有盛名,卻保有精進藝術之心,於是決定師從老生流派之余派宗師余叔岩。其台上風光,而私底下和梅蘭芳、杜月笙離合的情事,亦為人矚目。然最終與她相伴,惟有余派精煉之聲。
《女》從清末八國聯軍事件開端,慈禧率光緒等人西逃,幾年後重回帝都。返程中,回憶和現實不斷交替出現。過去的帝妃生活,二后奪權問政,和光緒因婚事、變法生嫌隙,處置義民團方式,依舊清晰;眼前則是逐漸衰老的肉體,無可迴避的終局。
人物主題式行為
《孟小冬》、《女王的名字》主角為女性公眾人物,編劇挖掘其私下形貌作特點。《孟》演孟小冬和梅、杜的相識過從,她如何成為丈夫的「妻子」;《女》將慈禧置於複雜的人際網絡:帝王夫妻、嬪妃姊妹、母子和婆媳,因上下半場劇情對映,演員互換角色,所以好幾個「母親」(平民、皇帝、天下之母)反覆出現。
但劇本不止步於這方面,再用過去社會中男性所求成就,作為二女的人生目標,與前述特點相表裡。《孟》中孟小冬學習雅正的余派老生,企圖接近男性創造的藝術境界;《女》中慈禧在子女婚姻、宮廷大戲和朝政上,展現指揮欲望,而古代權力競逐大多歸屬男性世界。
兩齣戲將主角放在倫理關係--某人之妻、之母,凸顯女性特色,亦藉這種普遍性身份,表現名角光環、位高權重下,她們也是普通人,試圖取得認同。同時描摹兩人的公共領域行動,有意突破舊時約束,不願局限女子於家庭內苑,僅具倫理身份而已。如果妻子、母親身份無助於成角兒、擴張權力,那麼捨棄也罷。
這種塑造方式,既用私生活事跡來引人注意,又有世人熟悉的公眾面貌,具備明確的主題式形象;相反來看,舊日女性的理想,尊崇的典範轉移,從賢妻良母標竿換到男人霸權裡爭勝,只是這些仍都由男性來定義,脫離不了審視。
舞台美術連結人物,表現時空感
《孟小冬》、《女王的名字》場面安排,運用道具連結人物行為,並劃分場上區域表現時空感。
《孟》在舞台中央靠後設置一平台,上面擺著單人用的桌椅,為孟小冬「敘述」經歷時站或坐之所;平台正前方,是孟和其他人「表演區」,呈現其提及的戲碼片段。《女》頻繁使用桌椅,特別是椅子,是人靜態動作的居所,以慈禧為例,舉凡敘事、看戲、聽政、休息都坐著;「表演區」常臨近上位者之座,有小欄杆圍在地面四周就是戲台,演戲中戲,無欄杆則成演員內心活動處。
戲裡不同造型、方位的座椅,有多種功能。首先是主角生命狀態,從椅子擺設位置來看,《孟》孟小冬鑽研余派唱腔,退居幕後固守孤獨。《女》慈禧無論宮城內外,始終居權位中心;二是對女性的傳統看法,出現椅子,暗示此處為室內空間,認為女人宜不出戶,反映社會「男主外,女主內」觀念;三是演出作用,人為主軸的戲,說書者需要坐著以便敘述。至於舞台區域,因劇情包含現在和過去,用簡單手法區別不一樣的時空,隱含戲和人生只在分界間之意。
這樣安排場面,應用戲曲原有道具,連接人物本身行為;因回憶產生的時空跳躍和繁雜事件,全藉虛擬化舞台想像,以及清楚地台上規劃,很簡潔完成調度。
演員和敘事角色設計
兩齣戲的表演,除了關係演員演技外,角色設計如何建立人物形象,也值得注意。
《孟》、《女》的主演都是魏海敏。前一齣,魏貫穿全劇演孟小冬,說台下人事如話家常,口條疾徐有餘,帶舊時代韻味;京劇老生、青衣行當轉換自如,比方戲中戲《四郎探母.坐宮》,一人分唱楊四郎、鐵鏡公主【西皮快板】;本劇尚有現代新編京腔音樂,她亦駕馭得當。後一齣,魏前半段演慈禧,然下半場劇情是上半場「鏡相」,含魏在內共六名演員交換角色,重現上半場。後半段她依次飾珍妃、光緒帝、義民團媽媽和慈安太后(魂),各有掌權者的威儀、年輕人的活力熱情與人民母親的平凡等氣質。
總體來說,魏海敏在《孟》展現戲曲跨行當的本領,《女》更多是戲劇的表現,跨界切換流暢從容,沒有勉強之狀。
此外,以歷史真人來作戲,誰來說故事/說書,會影響人的形貌。《孟》設定孟小冬是說書人,親身連說帶演,將昔日經歷攤開。因是國光劇團製作的戲,基於劇團本位與對京劇前輩的敬意,選擇從藝術角度來編寫人事,遂產生一致且正面形象。《女》是齣圍繞慈禧和相關人等的戲,除魏海敏以外,其他人擔任敘事工作,而戲劇演員徐堰玲是主述者,負責解說情節、內心想法與彌縫場次空白,並串演別的角色。於是形成一群旁觀者怎樣看慈禧、事件的個人視角,「女王」被每個人賦予各自觀感的「名字」,變得多重面向,也益加難以捉摸。
結論、戲說史觀
《孟小冬》、《女王的名字》的歷史、人物,具性別典範移轉特色,以及兩相對照各異其趣的史觀。
戲中人,在社會裡的性別學習典範,有從女性移到男性的現象。過往時代要求女人盡到妻子(某人的妻)、母親(他人之母)職責,然這些都是隸屬於別人的倫理身份。這裡卻不以「賢妻良母」看待主角,反而描寫她們走向藝術精萃、權力治術的人生頂端,趨於男性嚮往的成就。這是主創群透過史傳人物,京劇藝術家以自身為媒介,有意識展現非傳統、更多發展可能的女性。
戲說的歷史觀點,《孟》採當事人自述,類似個人歷史的「自傳」。雖是來自第一手資料/聲音,但能揭露幾分真實性,恐怕留有疑問,且只有一種敘事之聲,因此解讀史實時主觀性較強。
《女》由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製作,劇團以前作品常見對集體觀念、高大論述、流行偶像之拆解手法。本次創作者針對歷史,引入「記憶」說法,即所有清末人事,都是一場現代安養院為老人家舉辦的戲劇活動,院內失智症者輪流扮演女王(慈禧)。現代劇團用記憶不確定和戲劇虛構,把歷史當成一種趣意盎然的人造物[1],從而打破敘事的主觀性,但也使觀眾失去了相信的基礎。
歷史作題材,人物具明顯挑戰既定框架的特點,眾多史料能結合成完整故事,不失戲劇本質,對於何謂歷史、怎樣看法,也有特殊見解,使過去不再如舊,而有當代新詮的名字。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