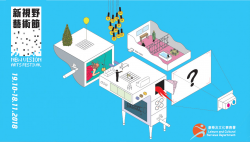 |
觀眾參與在香港近幾年的演出製作中成為寵兒,參與式劇場其門如市,筆者的日常工作是策劃、設計及帶領以戲劇為手法的工作坊或劇場製作,崗位不論是監製、戲劇指導、教育劇場節目策劃、演教員或工作坊導師,均令筆者對參與者的即時反應、行為模式、心理狀況、知性理解與判斷極感興趣,故本文將列舉一些筆者曾經經歷的觀眾參與事例,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對觀眾參與不同層面的討論。
觀眾走出來,演
論壇劇場先由演員演出被壓迫者處境的故事,然後邀請觀眾走上舞台,取代個別演員,透過戲劇行動或角色言語,嘗試改變被壓迫者的處境,體會並反思當中的不平等;負責主持及搭建演員與觀眾溝通橋樑的丑客(joker),亦以觀眾上台介入處境的行動及話語,引發觀眾一起討論與推演被壓迫者面對的種種阻力。這種先觀後演的參與方式,讓上台介入的觀眾成為觀演者(spect-actor),先觀看戲劇內容,進而以行動預演、應對、思考面對日常不公平狀況的做法與底蘊。
隱形劇場針對當地議題,通過演出引發在場者的即時議論及參與。透過預先設計的劇本,以及演員的即興對話,隱形劇場的團隊在非劇院的公眾地方進行相關展演,例如超市收銀處、馬路旁邊、地鐵車廂等,地點以人多聚集,易於引起在場人士(觀眾)議論為佳。雖然這是公開演出,但並不會事先張揚,甚至演出時亦絕不會顯露演員身分,故有隱形之特性,猶如隱蔽鏡頭的真人表演節目。劇情主要圍繞當地的社會問題,例如食品價格暴漲、交通擠塞、性別歧視等,透過幾位演員的鋪陳和牽引,情節漸漸引發衝突。過程中,旁觀的在場人士不其然捲入事件當中,觸發與演員或在場人士互相爭論,他們既是事件的旁觀者,亦成為事件的參與者、爭辯者、解決者,呈另一種觀演者的狀態。
觀.演並列,無限可能
將觀眾席位置轉變,令觀眾置身場景當中,成為表演文本的一部分,亦是觀眾參與的另一呈現。例如「阿姆斯特丹劇團」的《羅馬悲劇》鼓動眾多觀眾走上舞台坐在場景預設的大量梳化上,更鼓勵觀眾於數次轉場時間轉換位置:台上的轉到另一梳化、台下觀眾走上舞台找位置坐下、台下觀眾走到其他觀眾席坐下……觀眾自行選擇觀看的位置,台上的觀眾成為場景的一睿,幻化成場景中的群眾/人民。隨著劇情的發展,一位又一位君王(政治家)於政治戰役中敗亡,群眾成為時代的見證人;觀眾通過Twitter即時發表文字與圖畫,投影在台上的熒光幕,領袖受人民讚頌或唾棄,朝代更替,群眾成為推展劇情的關鍵,並且成為表演的共同演出者(co-performer)。
觀眾聆聽著耳機內容,遊走於不同街道、城市角落,里米尼紀錄劇團的《Remote X》系列於不同城市「因地制宜」的上演。每位觀眾聽著語音「人物」的話語,走進城市不同部分:在公眾地方跳舞/「郁動」、於跑道上競賽、選擇路口/左右街道行進、凝視路人……街景頓成舞台的場景,路上行人變為被觀看的演員;戴著耳機的觀眾聚成群體,穿梭城市,形成奇觀,成為行人的注視點,繼而形成被觀看的對象。演出沒有預設的演員,戴著耳機的觀眾成為受注目的表演者,而街上行人既是被觀察的表演者,又是注視奇觀的觀眾,觀者、表演者兩種身分同時呈現、重疊,進佔表演的主導位置。
藝術家違反劇場常規,引起觀眾的燥動與不安,引發思潮的起伏與行動的參與,延展作品主題的討論。謝洛姆.貝爾的《繼續跳舞》在開場時特長的燈暗與燈亮,襯托長時間空置的舞台,已讓觀眾感到漫長的等待。台前的DJ播放一首首流行音樂,素人舞者時而郁動身體,時而動也不動,時而凝視觀眾,粉碎了觀眾觀賞舞蹈表演的預期。2003年筆者在香港藝術節觀賞時,大多時間花在觀察觀眾在觀眾席上的舉動:靜默、嘆氣、竊竊私語、大笑、起身離場、離座引起椅子聲響、起身大聲指罵台上舞者、起身離座漫罵台上一切離開……台上台下場景並置並行,劇院內眾人的行動和參與,漫延至劇院外的評論與反思:高級精緻藝術與大眾文化、專業舞者與民眾的定義。誠然,不同年代的藝術家以作品作為對時代的叩問,均會挑戰觀賞的常規,刺激觀眾思考,引發議論與行動。投入、喜愛、憤怒、厭棄……觀眾參與的表現如何界定?參與和投入(engagement)是否等同?
主客以外,互文對話的交纏
傳統上觀眾處於觀眾席幽暗的空間,彷彿只是窺看舞台的演出,經常被認為是被動接收與接受的表現。然而,觀眾會自行尋找方法,接通戲劇虛擬世界的處境,行進劇作者的路徑,走出自己的觀賞體驗。2009年筆者於劇團工作時,邀請研究員譚寶芝博士對《昆蟲世界》學生專場進行青少年觀眾的審美回應個案研究,受訪的學生觀眾並非只沉醉於戲劇世界中,觀者會邊賞邊想,通過戲劇製作與作品及現實社會進行對話,從而發展自己的聲音與詮釋。例如:劇中的金龜喜大量儲備,受訪觀眾認為猶如人類喜愛金融、投機,盲目追求,惟金融風暴後,一切如煙。他們又憤慨劇中蟋蟀的見死不救、毒蜂的弱肉強食,省思自己(人類)的行為亦如動物般殘暴,並聯繫出不同的歷史事件作證,反思自身與當下社會應如何自處。觀眾處於戲劇虛實之間(metaxis),藉互文連結,透過比較、聯想、解釋、推論的思考方式,詮釋與評論戲劇及現實世界。觀眾藉作品為中介,處於感性與知性的參與。劇場創作人與觀眾是平等和不可分割,劇場是製作與觀賞的交遇與互動而生成,其中結合了藝術創作與審美體驗。(註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戲劇構作
本文列出的觀眾參與事例,相信在藝術家與觀眾的相遇與對話下,只是一鱗半爪。本文亦無意把以上事例籠統的界定為觀眾參與的不同方式,只希望引用事例中的肌理,匯集成觀眾參與跟戲劇創作的互為關係。參與已成為當代戲劇創作的重要元素,觀眾參與跟戲劇文本、空間、物件、人物、聲音、光線、科技、遊戲……交纏並列,構作出一部部藝術作品。然而,觀眾於劇場創作從來都佔有重要席位:亞里士多德探討悲劇系統如何讓觀眾淨化心靈,布莱希特以間離效果讓觀眾停止沉溺於戲劇、繼而反思社會,當代劇場觀眾置身參與其中,進行體驗、表演、反思、反諷、解決社會問題……觀眾的位置一直都在創作人心中經久不衰。
克萊兒.畢莎普總結了藝術家選用人群作為材料的不同理由:
「將日常行為重構成表演,以挑戰傳統的藝術判準;讓某些社會團體有能見度,以更複雜、直接而具有臨場感的方式渲染他們;引進機率和風險的美感效果;質疑現場和中介、即興和照本宣科、真實和做作的二元性;檢驗集體身分的構成,以及人們為什麼總會踰越這些範疇。」(註2)
與此同時,觀者從來都不是被動的接收者,觀者演者互為影響,共同參與及創建藝術經歷。審美歷程不能預設果效,卻受表演類型、社會文化、歷史時期等轉化成不同呈現的觀者美學(art of spectatorship),多變多樣的觀眾參與更會築建為觀者的戲劇構作(dramaturgy of spectatorship),交織於當代劇場的創作關鍵。(註3)
(註1)譚寶芝。2010。〈青少年觀眾的審美回應:以《昆蟲世界》作個案研究〉,《藝術教育研究》,第20期,頁67-92。
(註2)克萊兒.畢莎普著,林宏濤譯。2015。《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頁397。台北:典藏藝術家庭。
(註3)Fischer-Lickte, Erika. 2016. “The Art of Spectatorsh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Drama in English, Volume 4, Issue 1, p. 164-179.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