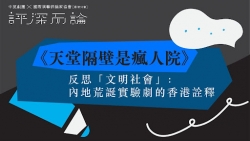 |
《天堂隔壁是瘋人院》——反思「文明社會」:內地荒誕實驗劇的香港詮釋
討論劇目:《天堂隔壁是瘋人院》
藝評人:李博文、王昊然
主持:陳國慧
文字整理:江祈穎
定稿:李博文、王昊然
《天堂隔壁是瘋人院》是內地著名編劇喻榮軍先生的代表作,是次於2025年8月在香港大會堂劇院順利公演,由中英劇團重新演繹,駐團導演林健峰之改編融入香港語境,為觀眾呈現了一個真假交錯的瘋人院世界。瘋狂與正常或許只隔一線,《天堂隔壁是瘋人院》以黑色幽默揭示人性的孤獨與荒謬。三位藝評人——李博文、王昊然和主持人陳國慧,透過討論該劇的身份焦慮、文化轉譯、劇本內核、二次創作、服裝舞台設計等方面,分析本次製作如何抽取原作精髓,並以本地視角注入新意,藉瘋狂嘲諷文明,引領觀眾在笑聲中思考社會現實。
喻榮軍早期作品富黑色幽默與荒誕意味
陳國慧指出劇本在內地很受歡迎,經常被不同劇團甚至學生團體搬演,因其強烈的玩味性,以及為導演和演員預留了大量的二次創作空間,使其能夠呼應當下的社會處境。李博文介紹了該劇的背景,指出《天堂隔壁是瘋人院》是資深編劇喻榮軍先生相對早期的作品,大約在1998年寫成,最初的名字叫做《無所顧忌》。該劇2001在年於上海首演時採用了現在的劇名,之後也曾在大阪公演過。在2010年的上海重演中,喻榮軍在「編劇的話」中曾以「找尋失去已久的身份」為題,探討作品的核心議題。
故事的主線圍繞主角無所展開,他極度渴望被他人聽見他說話。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他一開始就給予一個名叫波波的女生金錢,要求她專心聽他講話。隨著情節推進,他經歷了許多人與事,甚至曾被一名處長當作替身,讓他代替上司聽取某些東西。最終,無所決定去殺人,目的是為了被起訴、被調查、被錄口供,這樣就有人會專心聽他講話——可見劇情極富荒誕性,亦充滿轉折,無所在劇中甚至經歷了第一次被處決。劇本有一個關鍵的轉變,讓他獲得了再來一次的機會。在這次機會中,他與自己打算謀殺的人進行了交談,似乎被對方說服而放下槍。但最終卻發生了天意弄人的意外,他放下槍時,槍枝意外走火,射殺了自己。
角色身份焦慮 反映時代背景
王昊然分析,劇中關於身份焦慮的時代背景,可追溯到1980年代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當時中國經濟上對外開放,出口貿易蓬勃發展,到2000年左右,社會熱衷於討論加入WTO的事宜,積極推動全球化,這與現在的逆全球化環境非常不同。在這種環境下,社會大眾首先面對的是外來流行文化的衝擊。人們開始反思中國文化身份的安身立命之處。劇中的一個重要角色楊仁,便是這種文化焦慮的體現。他有經歷過在海外深造,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甚至帶有印度口音。他將自己包裝成一個高度「國際化」的人。在當時,社會上許多議題都圍繞著留學歸國人士,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此外,身份焦慮也源於內地的城市化進程。改革開放後,大量地方城市人口湧入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大城市外來人口眾多,導致本地人的身份感稀薄。加上學校從幼稚園或小學階段開始,推行「請講普通話」的標語,使得許多人慢慢淡忘了自己家鄉的語言。在不屬於自己的城市裡,人們對於自己的身份和歸屬感感到迷惘。這種身份焦慮,向內是關於地方性的逐漸淡忘,向外則是對於中國身份的宏觀迷茫狀態。
文化轉譯的廣東化與陌生化
本次香港的演出,語境從普通話轉譯為廣東話。李博文指出,導演林健峰和演員們下了許多功夫,將一些原本依賴內地語境的笑話或文化背景,例如午餐或學童相關的笑話,進行廣東化改編。如果只是純粹的文本直譯,這些笑點就會失去意義。
然而,這種轉譯也帶來了陌生化的效應。例如,劇中看門診的情節,用廣東話說會讓觀眾聯想到香港看門診的場景。但劇中描述醫生對於政府官員極其恭敬的態度,在香港的語境中卻是少見的,因此產生了陌生感。劇中楊仁對比里白的對話,展現了一種中外藝術形式的碰撞對撼。楊仁採用Rap的節奏,而里白則以古詩詞或較慢的方式唸對白。這種對比清晰地呈現了古代中國思想與帶著海歸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的文化衝突。
演出具追看性 雅俗共賞
王昊然表示,看完演出後十分驚喜,因為整個劇情很具追看性,觀眾都能跟上劇情。他認為這部戲屬於雅俗共賞,無論是想看鬧劇的觀眾,或是能細細品味台詞深度的讀書人,都會覺得有趣且有深度。雖然欣賞,但王昊然承認在觀看時有陌生的感覺。他很少在香港的廣東話語境中,聽到那些非常內地的描述。例如,劇中角色展現出極度謹小慎微的狀態,擔心得罪遠房親戚會連帶得罪科長。這種狀態在香港作品中相對少見,但在內地社會極重人情關係,靠關係討好上級的心理,是跨越地域限制的。
王昊然指出,這種內地現象的描述,雖然與香港社會融合得很厲害,但濃厚的內地語境在香港作品中是少見的。他對觀眾在聽聞這些內容時的會心微笑感到詫異。不過,李博文強調,正因為像上海一樣,香港也是一個對外開放的港口,所以同樣會面臨外來文化的流入,以及某種崇洋媚外的心態。因此,劇本嘲諷的人性共通點,例如辦公室政治中需要討好上司的心情,在不同地域是相類似的。
中英用心演繹瘋狂喜劇 風格獨特耳目一新
本次中英劇團的製作,導演和演員在排練過程中投入了大量心血進行再創作,加入了許多新的爛笑話。王昊然以韓紅的笑話為例,說明這些幽默元素經過精心研究,能夠找到合適的尺度,既能引起現場觀眾的大反應,又不具冒犯性。王昊然認為中英劇團這一版本成功呈現了一種瘋狂感,令他感到耳目一新。他覺得這種風格與他在內地見到的劇團風格不同,特別是在表演和導演層面,顯得比較純熟。
李博文從美學角度補充,舞台上的服裝設計風格走向了誇張化,以呼應荒誕風格的劇本。例如,律師楊仁的服飾採用綠色袍子,結合了自由女神像的形象。他同時被蒙上眼睛,手持一個單車頭懸掛著兩個膠袋,像徵法庭的天秤,並配備一把小刀,呈現出幽默的形象。醫生則穿著誇大的瘟疫醫生袍,配有長鼻子。這種誇張的手法配合非邏輯的對白,使得觀眾可以放下嚴肅的態度,接受這種瘋狂的風格。
陳國慧特別提到飾演主角的演員許晉邦,因為他本身也是編劇,對喜劇很有心得。許晉邦在舞台上展現了強烈的喜感,能夠在角色瘋狂的狀態中找到自己的邏輯。陳國慧認為他對節奏和形體的控制非常好,其自帶的喜感對於角色的推進非常有幫助。
女性角色發揮空間較小 演繹未見深度
王昊然指出,由於作品首演2001年,帶有較強的男性視覺,這使得女角的發揮空間相對較小。儘管波波這個角色在文本中很重要,李博文評論文愷霖飾演的波波略顯單一,僅呈現出她愛錢的一面,未能深入探討金錢對她的意義。他希望看到更多對波波善良一面的鋪排。陳國慧提到文愷霖飾演醫生時處理較有趣,無所強行將錢塞入箱子,醫生大喊無所後又馬上失去專注力,這與無所必須給錢波波才能換取她專注力聽他說話的關係相似。李博文認為,波波作為最後陪伴無所走完旅程的人,兩人雖然在結尾表達愛意:「波波我,波波我」,但其實他想說的是「我愛你」,但表達方式有點狡詐且好像傳達不了。
舞台上利用了假人裝置來製造效果。王昊然分析,假人有兩個功能。首先,在群像戲中,如一場類似《最後晚餐》的畫面,假人與真人混雜,讓觀眾難以辨認,起到了群體效果。其次,假人也參與了互動,例如在一段類似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的戲中,和無所與穿著旗袍的女性假人有所互動。
舞台元素眼花繚亂 符號太多使人難以聚焦
李博文認為舞台元素的運用有點眼花繚亂。他提到詩人里白的服裝,傳統應為白袍,但這次卻是鮮紅或橙色,令人感到違和。舞台上混合了多樣的音樂主題曲,如Mission Impossible的配樂、《花樣年華》和Queen的Bohemian Rhapsody。此外,無所受刑時還背著十字架,融入了宗教符號。
李博文指出,劇本原本就複雜,角色不斷切換。對於第一次進場的觀眾而言,要消化台詞已屬吃力。如果再加上太多混雜的符號和不同的意象,觀眾在眼花繚亂的舞台上試圖聚焦故事時,會感到辛苦,難以找到焦點。陳國慧反問,既然故事設定在瘋人院,舞台上的多重元素和色彩是否也因此順理成章。
總結
這次本地改編在節奏上明快,注入了許多新的文化元素和笑料,為觀眾帶來了一個愉快的觀劇體驗。陳國慧強調,喻榮軍的作品與香港淵源深厚。這次中英劇團的製作,透過香港元素的參與和變奏,成功讓這個劇本的內核含有跨地域的共通性,與香港文化語境進行了一場有趣的對話與對讀。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