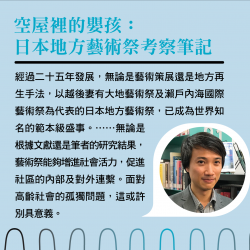2025年8月
前言
筆者開始執筆的前一天,剛從舉辦「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以下簡稱瀨戶藝)的日本香川縣回港。當地遇見的各地遊客,與社交媒體上看到的鋪天蓋地華文宣傳互相暉映。這是疫情後首次舉辦的瀨戶藝,不知道最終遊客數字會否突破紀錄?
從2013年開始,十多年來筆者一直針對瀨戶藝為主的日本地方藝術祭進行人類學考察與訪談,並憑此完成了兩個研究院學位。感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邀稿,並同意筆者以此為題撰寫評論。筆者希望藉此機會以非學術文章的形式,為華文世界讀者就此炙手可熱的題目分享一下觀察與見解。
瀨戶藝會期時的直島,遊客預早一小時排隊等待前往高松港的船,當地人員穿著祭典法被舉旗送別。照片攝於2025年5月27日。
一.何謂地方藝術祭?
日語中的「地方」,字典上的解釋之一是「中央」的相反詞,即是東京以外都可稱為「地方」。這定義無疑過於狹窄。而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的技術性定義,三大都市圈(即東京圈、大阪圈及名古屋圈)以外地域皆為「地方」,這定義亦較貼近一般用法。對於來自大都市的人來說,「地方」的想像大概就是生活不便的遙遠鄉下。日本全國人口自2008年開始逐年減少,加上自1950年代開始的鄉城人口轉移,今天日本大都市以外的地方皆面對嚴峻的人口危機。當人口迅速老化及減少,經濟及社會活力亦隨之式微。這是日本地方藝術祭的時代背景,而很多藝術祭正正是打著「地方再生」的旗號舉辦。
究竟日本全國有幾多個藝術祭?日本TBS電視台於一輯2015年9月的節目中提及,當時日本有超過一百個藝術祭。從2015年到2019年間,筆者於日本考察時則每每聽到「二、三百個左右」的說法。這裡有兩點值得留意。一,藝術祭本身不容易定義,加上全國曾經出現過由地方政府、財團、非牟利機構、大學或藝術家個人舉辦的藝術計劃規模不一,難以點算。二,雖然沒有實質數字,但是疫情前日本確是出現過全國藝術祭風潮。疫情過後,仍然有新的藝術祭陸續展開。
如果讀者有看過一些日本藝術祭的相片,該會留意到設置藝術品的場所:海邊、山中、空屋或廢校,與美術館或畫廊等傳統場地截然不同。類似的小型藝術項目,在二十世紀後期已經零星出現;大型地方藝術祭,公認的起源是自2000年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新潟縣十日町市及津南町;以下簡稱ETAT)。至於吸引更多遊客的瀨戶藝(香川縣主導),則先有倍樂生(Benesse)公司及相關的福武財團早於1990年代在直島開展的私營美術館計劃,到了2010年才與香川縣政府合作,逐屆發展成2025年環跨十一個離島、六個港口區域的大型藝術祭[1]。ETAT與瀨戶藝都是三年展,由北川富朗擔任藝術總監。如果與「威尼斯雙年展」等西方週期性藝術展相比,日本地方藝術祭的特色在於其廣大面積及鄉村特質。雖說如此,北川在其著作中提及早年自己曾經考察德國「documenta」及「Sculpture Projects Münster」,並受其影響[2]。筆者翻查2000年第一屆ETAT的指南及目錄集,當時ETAT的確是以戶外當代雕塑作品為主,與北川主理的1994年東京「FARET立川藝術計劃」,同樣有Sculpture Projects Münster的影子。到了2004年,日本發生新潟縣中越地震,導致當地房屋結構惡化,人口遷離加速,空屋處處。持續少子化,亦令到地區學校相繼關閉。自2006年的ETAT,主辦者刻意讓藝術家利用空屋及廢校進行藝術計劃及作品展示,而空屋及廢校的再利用亦成為往後日本地方藝術祭的一大特徵。對於地方政府當局來說,無論把廢校拆卸還是津貼市民拆掉空屋,都是財政負擔。透過藝術祭資金延續空屋及廢校的壽命,反而更合乎成本效益。這亦幫助塑造地方再生的正面形象。
二.藝評與藝術祭
當日本發展地方藝術祭之時,西方亦出現場域特定藝術(site-specific art)、關係藝術 (relational art)及社會參與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等概念的討論。當Miwon Kwon[3]、Nicolas Bourriaud[4]、Grant Kester[5][6]及Claire Bishop[7]等藝術史家、藝評家為相關概念進行闡述及辯論時,經常手法為引用個別相關(西方)藝術作品為例,加以分析評論,以支持自己的論點。Rirkrit Tiravanija的《Pad Thai》(1990)系列,便因此成為了關係藝術的代表作。這些西方藝術概念,一直影響著日本的藝術討論[8]。
個別藝術品可以評論,而日本亦不乏藝術展覽評論。另一方面,日本的大型藝術祭往往得到主流傳媒、流行雜誌及藝術刊物鋪天蓋地的宣傳,特別針對藝術品的深度評論卻較罕有。筆者認為,大型地方藝術祭對於藝評人及藝術史家帶來挑戰,原因在於其極端規模。就如關注日本藝術祭的美國藝術史家Justin Jesty所形容,歷年ETAT作品數以千計,「難以一概而論」(defies generalisation)[9]。筆者打個比喻:評論草間彌生藝術者,可以引用直島上的作品為例,與草間其他時期的作品作比較分析。同樣地,關注建築者,亦可以引用直島上安藤忠雄的建築,與安藤的其他建築一併討論。然而,像ETAT及瀨戶藝般的大型藝術祭,究竟要在歷年千百件作品中如何選取及分析,才能歸納其藝術本質,並加以理論化?
關於日本地方藝術祭,較常見的藝術批判是針對其「非批判性」。即是說,藝術祭作品偏重社會共創(co-creation),而缺乏政治及社會的批判元素。東京藝術大學教授熊倉純子以此帶出西方與日本的分別,沒有批評日本的意思[10]。而評論家藤田直哉於其〈前衛のゾンビたち──地域アートの諸問題〉(前衛的殭屍們:地域藝術的諸問題)一文中[11],則直接抨擊北川年輕時曾經活躍於社會運動,現在他的藝術祭卻為政府服務。筆者曾經於2020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中聽到紐約大學博士遴選人Eimi Tagore-Erwin的錄音發表,她以瀨戶藝公開徵集提案的文件為證據,指出藝術家須要配合當地文化、與居民共創,因而容易基於避免冒犯居民而陷於自我審查,故此作品亦欠缺批判性。Tagore-Erwin後來發表的學術論文,繼而指出藝術家被工具化,因而被政府、贊助商、旅遊業等多方面掣肘,同時亦未必真的與民共創,或得到居民支持[12]。
筆者於2017至2019年間,曾經訪問多位負責協助藝術祭作品製作的員工,及超過十位參展藝術家。眾多訪談中,幾乎沒有一位指出或承認有審查或自我審查的情況[13]。現在回想,「批判/非批判性」的爭議本身的合理性值得重新審視。一,「批判性」於西方現代及當代藝術無疑極其重要,但是為何日本當代藝術要全盤接收西方理論和價值觀?二,北川本身著作頗多,亦經常被邀請演講,當中可以了解他最常提及的不是甚麼西方理論,而是民俗學家宮本常一的著作及鶴見俊輔《限界藝術論》。筆者認為,北川以此對抗偏重複雜抽象思考的西方藝術理論,並批評源自西方的資本社會現代性;回歸五感,回歸大地,正是他的批判性的展現。三,要客觀評論藝術祭的非/批判性,筆者認為唯一方法是審視所有參展作品,這亦是困難所在。Tagore-Erwin批判的漏洞,在於瀨戶藝公開徵集提案,只佔整個藝術祭作品數量的很小部分。再者,由於藝術祭作品眾多,「難以一概而論」,無論論者要提出甚麼觀點幾乎都可以找到作品例子以作支持。以2025年應屆瀬戶藝正在展出的作品為例,你可以引草間彌生《Red Pumpkin》(2006;直島)作例子,批評藝術祭作品創作由上而下,與地區文化及居民沒有甚麼關係,我則可以引王文志《Embrace・Shodoshima》(2025;小豆島),指出島內居民及島外義工如何一起採集及處理數千根竹子,如何一起與藝術家團隊製作,及當中產生的跨國交流和友誼。如果你說王文志的作品只是創造了美美的空間,雖然與自然融合,卻毫無社會批判性,我又可以引田島征三《Life of N: 70 years on Oshima - A Room with a Wooden Pot》(2019;大島),說明藝術祭如何提供機會讓藝術家就國家不義作出強烈控訴。說到底,單純以個別例子為大型藝術祭定義,並加以批判,恐怕只會陷於單方論證(cherry picking)的謬誤。
左上:草間彌生《Red Pumpkin》(2006)。照片攝於2010年1月2日。
右上:王文志《Embrace・Shodoshima》(2025)。自2010年的每屆瀨戶藝,王文志均率領台灣團隊在小豆島中山地區製作龐大竹製藝術裝置,每次用上數千根竹子,需要當地居民及島外義工合力採伐及處理。照片攝於2025年5月16日。
下:田島征三《Life of N: 70 years on Oshima - A Room with a Wooden Pot》(2019)。大島是國立療養所大島青松園的所在地,始於1909年,乃麻風病患者及康復者的療養所。直到1996年為止,日本強制隔離麻風病患者及康復者,令很多人大半生失去自由。田島以藝術手法重現入所者N的人生遭遇,痛斥國家制度的不公義。照片攝於2019年8月11日。
三.地方再生與藝術祭
由於不少日本地方藝術祭得到官方支持,深入社區,並以地方再生作旗號,「究竟再生了甚麼」,自然成為各方面關注的課題。藤田直哉於上述文章中,直接批評藝術祭最多只是「鎮痛劑」,無力扭轉地方衰退。而自200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不少日本及外國學者以量性或質性研究,作出更為細膩的分析。筆者亦認為,以社會科學研究切入藝術祭議題,比純粹藝術評論更有意義和急切性。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要應對議會、居民及傳媒的質疑,最有效的方法或許是以數字說明事實。舉辦ETAT的新潟縣十日町市及津南町,總面積達760平方公里,比東京都23區還要大,現今人口卻不足五萬。根據官方紀錄,2000年首屆ETAT吸引了逾十六萬位入場者,而自2015年第六屆ETAT,每屆的入場數字均超過五十萬,即是人口的十倍以上,官方宣稱的經濟效果數以十億日圓計。至於號稱世界最大級的瀬戶藝,除了疫情時的2022年,自2010年開始每屆的官方入場人數皆達九十至一百多萬,而日本銀行亦每每為瀬戶藝計算經濟效益,提出數以百億日圓計的驚人數字,成為地區經濟再生的證據。
另一方面,人口數字亦經常用作地方再生的指標。日本地方人口減少問題嚴竣,人口跌勢難以逆轉。據筆者理解,沒有一個舉辦地方藝術祭的地區、集落或島嶼會因為藝術祭而錄得人口增長。而藝術祭主辦者往往強調的,則是移住者(包括回流者及外來移民)個案。瀨戶內海的男木島,則是最經常被引用的例子。1955年,男木島的人口為1055人[14],現在卻只有132人[15],看似是典型的衰落社區。然而,瀬戶藝吸引到一些有志之士回流及移住,促成原本關閉的島上學校於2014年重開,方便更多的家庭移入。自2014年至今,計有一百位人士移入島上,當中有六十位成功定居[16]。如果132位居民中有六十位是年輕移民[17],那麼地方再生的成績則非常亮麗。
自2014年男木學校重開至今,筆者在不同場合及渠道重複接觸相關介紹。筆者於2010年首次踏足香川縣政府所在的高松市,至今亦見證了它如何從很普通的地方城市發展成國際航線再三增加、新酒店不斷落成的熱門旅遊點。然而,筆者認為男木島只是很幸運的個別例子[18],而高松市的發展亦不代表離島居民能夠受惠。據筆者理解,除了受倍樂生公司/福武財團關顧、著名美術館全年開放的直島及豐島,又或男木島這特殊例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週期性的藝術祭無法製造恆常就業機會,亦因而難以吸引足夠外來人定居,解決人口問題。
歸根究底,當代藝術和地方再生,有何關係?筆者在不止一次的座談會中,聽到北川如此比喻:「藝術就猶如初生嬰孩,很脆弱,所以可以令到不同人士前來,一起照顧。」如是者,來自四方八面、背景迴異的陌生人,一起來到遙遠的廢置空屋,為名叫藝術的嬰孩勞碌,慢慢建立跨區跨國人際關係。
無獨有偶,人際關係正正是關注藝術祭的日本學者的重點研究議題之一。精簡地說,這些學者大都基於Robert D. Putnam的社會資本理論[19],嘗試以量性或質性手法探究藝術祭有否促進社區內部中的連結,以及內部與外間的關係。雖然各研究的手法、對象及結論有異,但是筆者至今從沒見過,對藝術祭促進社會連結作全面否定的研究結果。
筆者覺得,外國學者及評論者最容易忽視的,是藝術祭的背後運作如何與居民長年連接。首先,無論是ETAT或瀬戶藝,都有類似的架構:地方政府主導行政,北川的公司(Art Front Gallery)主導藝術決策和製作,並設置非牟利機構(NPO)負責其他事宜。除了在藝術祭時期參與管理國內外義工,ETAT的NPO[20]負責全年管理藝術祭的所有相關場館,而各場館便成為連結附近集落居民的據點。此NPO的員工中有幾位女性,除了日常工作,同時亦是FC越後妻有女子足球隊成員,參加縣級聯賽。筆者當初對以藝術祭名義成立女子足球隊感到很莫名其妙,然而在2024年的田野考察中遇到當地居民表示,會追隨足球隊的比賽,為對方打氣。至於筆者更深入考察的瀬戶藝,當地NPO[21]除了直接管理義工團隊,亦會全年參與及支援各島嶼的傳統祭典和其他活動。位於豐島的藝術品兼餐廳「Shima Kitchen」,由NPO直接營運,亦成為了NPO連結島上三個不同集落的中心。除了每月舉辦以全島居民為對象的生日會,疫情前Shima Kitchen亦會定期舉辦「お惣菜の日」(小菜日),讓島民預先訂購簡單小菜,並由NPO職員逐戶送上[22]。2017年筆者有機會跟隨職員一起送餐,發現當時島民特別喜歡炸薯餅,甚至有人一口氣訂了二十個。據職員解釋,因為烹調油炸食品有危險性,所以島上的年邁者寧願待機訂購。當天筆者的另一領悟是,NPO職員藉著送餐,得以令平時深居簡出的老人定期打開家門,寒暄一下。這都是藝術祭帶挈的社會連結。
隨著時間流逝,地方政府職員不斷調職,而北川旗下公司的職員在全國不斷走動,兼且不免有人事變動。只有NPO職員,能夠長年貼近居民,這正是整個藝術祭架構的精要所在。據筆者了解,一些相對小型的日本地方藝術祭亦有類似設置,成效有待觀察驗證。
總結:給香港的啓示
經過二十五年發展,無論是藝術策展還是地方再生手法,以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及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為代表的日本地方藝術祭,已成為世界知名的範本級盛事。然而,藝術祭規模龐大,千百計作品風格迴異,若要公允的作整體藝術評論,實在不易。另一方面,藝術祭的地方再生成果,亦引來多方關注。論經濟效果,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及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的主辦者均宣稱達到龐大效益。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對於居民來說,往往只有從事旅遊相關行業才能直接得益。市中心或許因此得以發展,然而一些偏遠村落雖然設置藝術品,其實居民並沒有在經濟上直接受惠。再者,藝術祭的週期性,亦不利於在偏遠地區創造恆常就業機會。亦因此,根據筆者長期實地考察,藝術祭於人口再生上的正面效果,亦只有個別例子。當日本全國人口減少,個別偏遠地方要扭轉趨勢達到人口正增長,難度極高。最後,無論是根據文獻還是筆者的研究結果,藝術祭能夠增進社會活力,促進社區的內部及對外連繫。面對高齡社會的孤獨問題,這或許別具意義。如果藤田直哉硬要說這只是「鎮痛劑」,那麼起碼這「鎮痛劑」是有效的。
那麼,香港的「西貢海藝術節」呢?
香港政府首次於2018年財政預算案,宣佈旅遊事務署將參考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於2019年在西貢鹽田梓舉辦藝術祭[23]。當時旅遊事務署委託本地團隊文化葫蘆策劃,經歷疫情,計劃於2021年中完成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署方委託另一團隊One Bite策劃,擴大版圖,於2022、2023及2024年舉辦三屆西貢海藝術節。按2025年中的傳媒報導,藝術節因資源問題停辦一年,而有關當局「正檢視活動經驗和回饋」[24]。
筆者認為,藝術節涉及公帑,與日本地方藝術祭一樣,受各方審視成本效益是自然不過。然而,政府作為舉辦者,目標是甚麼呢?根據同一報導,三屆西貢海藝術節共吸引約21.4萬人次,即是每屆七萬人左右。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19年訪問旅客達五千五百萬,疫情過後,2024年數字亦回復至四千四百萬。對香港整體來說,七萬人或許意義不大。對於西貢碼頭一帶商家來說,這數字或許頗為亮麗。對於人口稀少的西貢離島社區來說,這數字卻相當龐大。然而,根據筆者自2021年的逐年考察,當地社區能夠吸收相關經濟效益的產業屈指可數,而每屆數週的藝術節亦未至於足夠創造持續經濟機會。這與很多舉辦藝術祭的日本地方,情況類似。若果要單單靠藝術節復興經濟產業,恐怕事與願違。
相對於西方週期性藝術展,日本地方藝術祭的另一特點,是由同一策展團隊長年經營,北川富朗策劃的藝術祭尤甚。這情況在全球藝壇相當特殊,放在日本地方脈絡卻有其道理:如果團隊不斷更換,如何能夠與居民建立信任關係,一起共創,達社會再生之效?鹽田梓/西貢海藝術節每三年更換團隊,重新招標審視,符合政府項目的一貫做法。然而,如果當局把藝術節看作為社會文化項目而不是旅遊經濟項目,三年時間未必能夠讓相關團隊做出成績。無論是文化葫蘆還是One Bite,均有人讚賞有人批評,筆者不在此評論。只是,任何團隊,其實都需要時間學習成長。
筆者曾經在日本走訪另一個小型地方藝術祭,該藝術祭每屆只吸引數萬位入場者,與那些數以十萬百萬級的大型藝術祭大相逕庭。當筆者在訪問中向相關負責政府職員提及數字問題,對方斬釘截鐵的說,從一開始該地方政府舉辦藝術祭就是為了社區活化,讓居民參與,對入場人次之類根本不以為然。目標明確,期望合理,才能夠適切的審視;長期堅持,才得以迎接開花結果。
(以上照片由作者提供)
[1] 2025年第六屆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會場,春、夏、秋三季參與的有直島、豐島、女木島、男木島、小豆島、大島、犬島、高松港區域及宇野港區域。另外,瀬戶大橋區域只參與春會期,志度・津田區域及引田區域只參與夏會期,本島、高見島、栗島、伊吹島及宇多津區域只參與秋會期。論參展會場數目及背後涉及的各地方政府,這是歷來規模最大的瀨戶藝。
[2] Kitagawa, Fram. 2015. Art Place Japan: The Echigo-Tsumari Art Triennale and the Vision to Reconnect Art and Nature. New York, N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3] Kwon, Miwon. 2002. One Place After Another: Site-Specific Art and Loc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4] Bourriaud, Nicolas. 2002. Relational Aesthetics (Simon Pleasance and Fronza Woods, Trans.). Dijon: Les presses du rée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8)
[5] Kester, Grant H. 2004. Conversation Pieces: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Ar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 Kester, Grant H. 2011. The One and the Many: Contemporary Collaborative Art in a Global Contex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7] Bishop, Claire. 2012. 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 London: Verso.
[8] 關於日本和西方的相關概念發展脈絡與關係,請參考:楊天帥。2019。〈日本正在做「社會參與藝術」嗎?〉,載於亞洲藝術文獻庫。https://aaa.org.hk/tc/like-a-fever/like-a-fever/is-it-socially-engaged-art-the-debate-over-art-projects-in-japan
[9] Jesty, Justin. 2021. “Japan’s Rural Art Festivals: The Echigo-Tsumari Paradigm”. In Cameron Cartiere and Leon Tan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rt in the Public Realm (pp. 23-36). New York, NY: Routledge.
[10] 非日文讀者可以參考:Kumakura, Sumiko and Nagatsu, Yūichirō (The Art Project Research Group). 2015. An Overview of Art Projects in Japan: A Society That Co-Creates with Art. Tokyo: Arts Council Tokyo.
[11] 藤田直哉。2016。〈前衛のゾンビたち──地域アートの諸問題〉,載於藤田直哉編:《地域アート : 美学/制度/日本》(頁11-44)。八王子:堀之内出版。
[12] Tagore-Erwin, Eimi. 2024. “Art festivals in Japan: Fueling, revitalization, tourism, and self-censorship”. Contemporary Japan, 36(1): 7-19.
[13] 只有一位海外藝術家,訴苦說自己提出的一些活動沒有達成,有被審查之嫌。筆者向相關職員求證,並依據長年在地田野經驗,認為純粹是資源及溝通問題。
[14] 引自〈(島に生きる:番外編)島ライター・斎藤潤さんに聞く 都会と逆の価値観育つ/香川県〉,《朝日新聞(香川縣)》,2015年12月25日。
[15] 北川フラム、瀬戸内国際芸術祭実行委員会監修。2025。《瀬戸内国際芸術祭2025公式ガイドブック》。東京:美術出版社。
[16]〈離島復活、挑んだ移住者 学校再開・伝統継続、ぶつかり合いながら〉,《朝日新聞(夕刊)》,2025年7月28日。
[17] 這裡指的主要是國內移民,不過直島和男木島等地區亦有個別外國人移民案例。
[18] 根據筆者考察,這與島上個別人士的超凡意志及能力不無關係。
[19] 例如: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 正式名稱為「NPO法人越後妻有里山協働機構」。
[21] 正式名稱為「NPO Setouchi Koebi Network」。筆者曾於2016年受聘於此機構兩個月。
[22] 自從疫情開始,改變成「便當日」,讓島民訂購便當。
[23]〈旅業撥款3.96億 海洋公園獲撥3.1億 派1萬學生門票〉,《明報》,2018年3月1日。
[24]〈藝術節暫停辦 村民接力免斷纜 政府:檢視活動回饋 議員嘆可惜消息稱無關財赤〉,《明報》,2025年6月8日。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