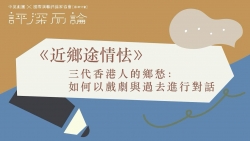討論劇目:《近鄉途情怯》
藝評人:鍾肇熙、小西
主持:陳國慧
初稿整理:江祈穎
定稿:鍾肇熙、小西
《近鄉途情怯》(下稱《近》)於1月在葵青劇院演藝廳順利公演,延續1992年張達明編寫的《客鄉途情遠》(下稱《客》),由資深劇場人劉浩翔續寫故事,中英劇團跨世代演員同台演出,揭示不同年代的人對「家」和「根」的感受。新舊關係密不可分,這作品在當年有看過演出的資深觀眾與新觀眾的目光裡,都會有其自己的詮釋及共鳴。這次「評深而論」邀請了資深評論人小西和劇場構作及導演鍾肇熙來進行討論,兩人來自不同年齡層,於不同年代開始欣賞中英劇團的作品,聯同主持陳國慧三位藝評人,透過比較兩個劇目的同與異,從劇本的視點轉換、兩代演員的演繹、舞台空間的運用等方向,分析是次製作如何連繫橫跨三十多年的尋根故事。
上下半場相隔多年,其框架都在說一家三口的家庭故事,不同年代的人們都要散居各地,上半場濃縮呈現《客》,本來生活在香港的爸爸俊叔,決定要回內地鄉下娶年輕老婆,同時間大兒子阿德決定移民加拿大,留下小兒子阿偉在港,他們三個在離愁別緒期間,和來自荷蘭的表妹阿年一起回鄉,從而對鄉下產生特別的看法,直面這家人拆散三地的問題。下半場以未來時空延續家的故事,三十年後Raymond 帶爸爸阿德回香港,我們知道原來阿德已經離婚,但因為要見親戚朋友,就要與前妻May假裝沒有離婚,後來一家三口回鄉探親時,Raymond重新理解鄉下,就算不在這裡出生亦未曾生活過,但都有某種情感聯繫,使他很想用自己的知識或能力貢獻鄉下,所以他選擇留在大陸。父子又要分開,又重新面對離愁別緒。 不同年代的人要經歷很多離異,家人因為不同原因要分散異地時,如何面對這種感情,所謂的家是實體存在,還是一種情感聯繫?
新舊劇作對比,既有呼應,也有視點轉移
小西看過《客》的錄像及劇本,回想張達明寫在1992年,明顯對應著當年的移民潮,對如何去建構一個家有自己的看法,《近》下半場設定在2030年,但裡面探討的離散議題或家的存在,都有不同程度的共鳴及感觸。小西認為《客》由頭到尾都是阿德的視點,《近》與其說續寫,不如說是由Raymond的視點重新演繹,上半場透過加插Raymond拍攝下的老阿德的回憶在故事裡面,為他和爸爸叔叔回鄉的劇情提供了背景,而上半場《客》中荷蘭來的那位阿年,轉變成老阿德的視點,兩個劇本之間的轉變有很多刻意對應,這是在張達明和劉浩翔的訪問中提到的。
鍾肇熙亦有看《客》錄影,當中笑鬧中見溫情,令人有喜劇的感覺,《近》喜感減輕,但更富情懷塑造。看《近》上半場時感覺較遙遠,像小時候看80年代的舊港產片,都會討論到回鄉,鄉下有很多香港難得一見的異象,變成為一些笑點,就是這種港產片的感覺。確實上半場個別小角色的處理都很強烈,很有喜劇色彩的瘋狂有趣,他們在特別的地方生活,會關注更多角色的擔憂,或者人與人之間的角力。到了下半場時,突然回歸到很強烈的90年代港產賀歲片氛圍中,大家單純直接的交流,兩兄弟之間嘻哈討論。看完戲會想世界是否這麼簡單,但是看的過程裡面,鍾肇熙嘗試說服自己現在要開心一下,回顧一下,看了整個演出,又有愉快的一個晚上。
道出近百年來華人的離散現象
小西認為《近》最後一幕圓月投影,最能捕捉到那種離散的感覺,基本上代表著近百年來華人整個離散的歷史,戲裡出現的所有角色,都拖著行李箱穿上戲服出來,每一個人的離散基於不同原因,由香港移居去外國,又或者由內地移居香港,成為離散的混合體。他們都會因為某些原因回頭看過去,他不一定是回頭看大陸某個鄉下,例如阿May主要是回頭看某個時代的香港。
即使未經歷過的過去,譬如戲裡最年輕的Raymond,之前沒有去過內地,香港出生而主要都在加拿大成長,但他在有些位置會回看鄉下。其實這在《客》裡是阿年的角色,她也是香港出生,但在荷蘭長大,對香港沒有特別的認同感,然後回頭看,覺得生命裡有一些若有所失,想找回一個「根」,這個根在舊版本裡是曖昧的,裡面有句對白大概意思是,「我回到這個地方,然後發現這個地方不是我的故鄉,雖然那裡有一些我認識的華人,那個地方叫做中國。」
近未來時空分野未夠清晰
陳國慧認為《客》在1992年面對回歸及中國想像,時間脈絡是比較清晰的。《近》續寫時的流動性則比較強,當中的「故鄉」其實較模糊,可能反映2030年時人對於身分的流動性,甚至家的流動性都有不同的想像。鍾肇熙也覺得這個時間點設定得很有趣,2030是近未來,當在戲劇上使用近未來,其實會有某種幻想,或想拉遠跟現在的距離,但觀賞經驗裡和我們身處的環境很接近,那遠一點的科技想像,甚至他們的語言運用,其實很影響我們怎樣看待戲中人。
下半場說去內地買樓花最後變成爛尾樓,其實在最近這十年偶有發生,甚至是舊聞,令我疑惑2030年這個時空,會不會是想把時間處理得不是那麼線性,幾年後回頭看事物,反而變舊了。這似乎在捕捉家的不確定狀態,在《客》中無論他們認不認同,喜不喜歡那個家,離開與否也好,都很確定那是根、故鄉,但到了《近》反而變得不確定,因為大家經過這個旅程,都有好結局,然後開心進入下個人生階段,安居他方了。
小西認為《近》對根的詮釋比《客》更深入,覺得能對比阿年與俊叔的角色,看出對家鄉認同的變化。《近》中老阿德講有關碑石的對白:「在那條村裡面,很多人在這裡生、在這裡死,所以這裡是鄉下。」在《客》中其實是阿年的對白,再加上她還有那段上述提及的對白:「我回到這個地方,然後發現這個地方不是我的故鄉,雖然那裡有一些我認識的華人,那個地方叫做中國。」這對白在劇本刪去,但在演出又放了回去,猜測達明在當時作為中生代,對家的態度是曖昧的,這已經有差異在裡面,這種差異在《近》中反而更加清楚而多元。
資深演員與新演員在舞台上擦出不同火花
演員演繹上,陳國慧認為有承傳的策略在其中,《近》很多演員都曾是《客》的演員,多數都是中英的資深演員,亦是現時香港重要的演員,陳國慧指那是她剛學如何看戲時,了解戲劇一個重要窗口,90年代中英演員關係如一家人般密切,這反映到表演上,他們的默契和火花到今天還很有印象,今次下半場看到兩兄弟在沙發上再見面,就算只是普通地坐著都很有戲,交流節奏很好,使人有種懷舊情緒而深有感觸。《近》加入了一些現在的中英成員,所以幾代中英演員之間的演繹分別,在風格上有不同的層次,在舞台上出現不同的火花。
不同年紀與資歷的演員,要在上半場飾演年紀差不多的角色,鍾肇熙看出演繹上分別很大,資深演員在演出的articulation會比較清楚而乾淨,情緒變化相當清晰,而新一代演員相對比較自然主義式,比較由內在出發,這分別不會使人覺得突兀,但資深演員演年輕角色,感覺割裂,例如阿德阿偉要與年青演員白清瑩飾演的阿年作表兄妹關係時,這一玩樂效果上變成兩個叔叔調戲少女。到下半場兩人已五十歲,演員做回自己年紀時,他和其他年青演員交流就令人很舒服。
陳國慧認為由同一個演員飾演兩個時空是可行的,因為《客》中阿德、阿偉都是由現在這兩位演員飾演,這個意義亦很重要,但事實上他們裝扮上沒有任何轉變,甚至形體變化都不明顯,所以除了表演上探索更多可能性,在視覺上是有必要調整。小西亦認為上半場有點尷尬,周偉強做年輕阿德時,他們不是全部戴上假髮裝扮,有一個原裝正版的老阿德在說幾十年前的事,然後盧俊豪戴了假髮扮年輕阿偉,然後旁邊有真的很年輕的表妹,如果選擇年輕的阿德、阿偉都由年輕的演員去做,甚至阿德由Raymond這個演員去做,可能會好一點,亦能保持得到繼成、傳承的意義。新的中英演員在演繹上的不同落差,或因為年代不同而令情感投入度有分別,這45週年紀念能有這樣的跨代合作,令到新演員有所反思,其實是一個好嘗試。除了演員,小西提到導演張可堅亦與年輕導演林健峰的跨代合作,這個戲是關於懷舊,而整個製作本身都很懷舊。
以錄像技術帶出移民二代視角
陳國慧看時沒有特別留意2030年的距離感,亦不很清楚Vision Pro,但那似乎令錄像變成重要元素,由開場到尾聲都在使用。開場時有一個錄像,看到Raymond以一個視角去處理一段回憶,令故事有不同層次及切入點。鍾肇熙認為整個上半場是Raymond嘗試透過他的拍攝去想像很多年前,爸爸回鄉遇到的狀況。
下半場主要的是在阿德怎樣面對家鄉以及兒子要去大陸工作這件事,而Raymond也是活躍的角色,提供了年青一代的聲音去反思,他拍攝現場影片作記錄,或後面裝作是Vision Pro的視像會議,其中最有效是他在後面翻族譜,透過他的視覺看到一代一代的人,由他爺爺到爸爸兩兄弟,再到他自己的名字被人硬生生地翻譯成中文名,借助這個族譜的影片,他出來去講怎樣看待鄉下的獨白,這能幫觀眾用Raymond的視覺去看這個戲。但當中都會令人疑惑那些視角是誰的,例如從低角度穿過那些稻草很遠處拍過去,那些角度是從哪裏來?後面那些小模型的部分是屬於哪個人的視覺?
上半場影片是現場直播,大概都是Raymond的視覺,但到下半場老阿德和老阿偉在梳化對話時,小西留意兩人的動作延遲,錄像技術延遲讓觀眾有種Cold Media的感覺,不是令人很投入,這個媒體剛好帶出又近又遠的距離感,呈現了Raymond對故鄉這件事的曖昧,他用藤掕瓜瓜掕藤這個意象,但到最後我們都不清楚他回鄉的目的,這種既近又遠的距離感,在不同世代與處境下延續了下去。
空間營造刻意平面化,營造回憶感
《客》演出時場地較小,且有很多台架,前後高低較大差距,不方便用路軌,所以演員較多高低走動,重心上亦多變化,較為立體。《近》則在比較大的葵青劇院,用了很多路軌,將一些行李箱或場景推出來,但陳國慧認為此佈置未太有效地處理到空間。事實上很多場景都比較靜態,空間運用中較多空白之處。上半場很多空間調動都利用到了箱子,透過移動很快箱子做出新的佈置,打開箱子後彈出草來就成為鄉下的草田。小西發現上半場所有人的褲腳或者行李箱,都有一點點稻穗在上面,就呼應根,腳在根,根在地。
《近》的舞台設計為回應影片拍攝,清楚有三個框,整個能量流動相當不同。鍾肇熙認為這空間變換相當空虛而且平面。加上開場Raymond拍攝的畫面下,可能刻意營造在一個屏幕看影片,故平面而缺乏深度,然後演員望向觀眾及對話,這是有意為之的,下半場開始實景,顏色對比較為明亮,實景都是推出來,但現在有梳化餐桌出現。
未能以語言特色表現地域隔閡
《近》環跨不同地域,回鄉的場景就有鄉音的語言,有一些鄉下話令我們意識到氛圍的建構,但陳國慧認為其他語言比較接近,我們不太聽到在海外長期逗留的那一代,廣東話是不是比較純正,大家仍然期待著可以更好。鍾肇熙認同語言特色不足,難以透過語言見到關係上的不同。家人離開後分隔異地,但在加拿大生活了30年之後再回來,就有所不同了,語言聽起來應要有點不舒服,疑問他為何這樣說話呢?這轉變能幫演員表演,但現在少了這個工具去看角色,可能因為上半場始終是來自《客》,未必可以大幅修改,只能從字眼上去修正。
時間的跨度語言中佔重要位置,如回看十年前自己的文章,某些字眼現在已經很少運用,例如「甕缸」,這些字眼不是現在這個年紀的人的常用詞,但父母日常會用的字眼,所以使用這些字眼會感到溫馨,更加扣連到整個戲裡問甚麼是家,你怎樣意識到我回家,有個人說回到家的意思是,我走出門口,那些人跟我打招呼,我是聽得懂的,我就知道這就是家,但其實相對大家用的語言,無論用字發聲都很接近,反而缺少了差異感,未有更多有趣的事情發生。
小西覺得《客》比較清楚,因為它有兩次歸鄉,裡面有個回憶沒有提過,就是70年代尾,俊叔與第一個老婆第一次回鄉,鄉下和香港的差異比較大,而語言上,鄉下話不同於當時香港人說的廣東話,現在內地的廣府話和香港的廣東話都有分別的。但是《近》就只提了90年代第二次回鄉,其實家鄉都開始變化,內地和香港的距離比較拉近一點,再到2030年時,新一代在加拿大長大,他講的廣東話會怎樣?甚至阿年五歲已經去了荷蘭,其實她說的廣東話也是不同的,但現在是頗純正的廣東話。所以語言分別在《客》比較清楚,《近》反而在一些海外華人講的廣東話之間,呈現很微妙的差異性,少一點語言探索。小西記得達明都有提過寫《客》時,他有故意回鄉,去觀察他們的表親講的語言是怎樣的,這個位置如可再進一步發展,其實發揮空間可以很大。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