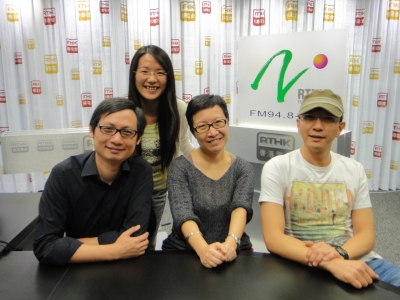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在二零一九年向《蘋果日報》辭筆,消息引起了不少文化界朋友「花生」(旁觀)看戲,有人在臉書認真撰文而《明報》「世紀版」甚至全版討論為何梁會追不上「時代」。這次辭筆事件,令我想起年輕的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作為藝評人,曾經如何探索藝評與公共領域的關係,而以劇場作為他其中一個實踐場域。這可能就是劇評人鄧正健在《為什麼梁文道令人討厭?》一文中說的「當年他仍是一個公共知識的先行者,讀他的文字,不只是年輕一輩,連他的同代人或長輩也看到未來的可能性」的梁文道,或其實是想及,整個藝評生態的轉化與游移,或我,作為在參與和推動演藝評論的一分子,在模塑公共領域的可能性上,是否能做得更多,和更有想像力。
據說梁曾經「實驗」過一個行為,因當時藝評在紙媒發表的速度太慢,演期又短,他試過在首演後把文章寫完影印,然後翌晚在演出場地派予觀眾。我不知道當時觀眾反應如何,但這個行為跨過了所有機制,創建了藝評與藝評人直接面對群眾(包括創作人與觀眾)的公共空間,可以即時產生對話與討論的可能性,即使藝評在當時的媒體已經具相當程度的可見度,但由藝評人自己製造空間和把藝評與藝評人「被看見」,而這空間又有意識地不只是一個讓意見私下交流的場域,這張不屬於任何機制的影印紙,有好一段時間令我覺得是不能承受的重,它以個人的力量嘗試扭動發表的可能性與公共性。
那個資助制度在起步的時候,正如當時活躍的香港實驗劇團「沙磚上」的仝人在《香港戲劇史個案研探──沙磚上:實驗.組合.時代》的訪問所言,資助在扶植發展的背後,是否亦同時消弭了創意與想像。《劇場公共領域》一書提及當審查制度終止,劇場享自由創作,敏感課題反而帶動不了公共討論而轉向美學探索;同樣為了應付接受資助的機制(如照顧票房、觀眾拓展等考慮),思考劇場及其公共性的力度,可能也會不自覺受限。「沙磚上」部分成員受「進念.二十面體」的影響,現在回想,兩者當時同樣在作品議題、形式、表演空間和舞台美學上,思考與探索劇場怎樣成為公共領域,於回歸前討論民主、制度、文化與身份;有趣的是這兩個劇團當中不少成員當時亦是活躍的藝評人(包括梁),他們在創作與媒體論述的互相碰撞下,讓劇場進一步與社會聯繫;而影印紙的實驗行為,多少有「沙磚上」和「進念」的影子。
《沙磚上:實驗.組合.時代——香港戲劇史個案研探》一書之訪問照。
與「進念」關係密切的林奕華,在那時期的創作與「教育劇場」更是有策略地在公眾間製造議題。劇評人林克歡在《消費時代的戲劇》一書中說:「林奕華往往將創作、演出作為一個完整的過程來呈現,這過程包括工作坊、前期的宣傳攻勢、舞台演出和演後座談會等資訊回饋。他的劇名、演出海報、宣傳口號、演出前訪談,大多是有意識地觸犯禁忌,有意識地逸出常軌:同性戀、裸體、性倒錯……」;其作品本身就是評論,這些論述根本不受限於舞台,舞台外的公共領域才是他要挑戰的空間。他在《用戲劇評論社會》的專訪中表示:「劇場不只在回應社會,甚至是在評論社會,目的是告訴觀眾:我們不是那麼被動的,也不只是社會的一顆螺絲釘而已。」
熟悉媒體文化和報導者與讀者心理,在當時紙媒報刊仍然是大眾獲取訊息、知識和創建公共關注與討論的黃金年代,林奕華在「主動地」批判和挑戰的同時,他不避諱讓劇場政治化,甚至樂於使之成為「事件」而不只是文化版一角的宣傳報導。香港劇場直到今天,絕少有創作人能像當年的林奕華般思考劇場及其公共性;當然創作人本身還要能力創造話語,迎向被置放在公共桌面上而不只是劇場茶杯裡的討論。二零一七年克羅地亞裔導演Oliver Frljić在波蘭透過劇場《詛咒》揭示當地教會的黑暗行為,作品爭議不斷後來演出也被禁,事後他在視頻的說法顯見他創作的鮮明動機;讓劇場成為「事件」所引起的(不能預期)的「負面」果效,在這個網路資訊如此迅捷、即食卻「愛黑特」的年代,作品除了要有更「爆」的主題和形式,創作人還要更有策略地轉「負」為「型」,如在歐陸極紅的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就交出了一張令觀眾既愛又惱的亮麗成績單。
誠然現在有些禁忌已視平常,大眾對一般議題更難在網路平台輕易買賬,不過議題卻從不缺貨;在這現實情況下,劇場可能是比前更難創造一種公共領域,但觀眾在網路文化下的迷失,卻更願意朝向找尋「意見領袖」(KOL),有看法和立場肯定要比中立來得更迷人。米洛.勞在《挑戰社會禁忌、觸碰道德底線》的專訪中表示:「自己的工作方式為『殘酷劇場』,殘酷,意味著揭露現實表面,勇於面對禁忌」,他取材自真實事件的「真實劇場」(Theatre of the Real)所帶著的懾人魅力,混合著觸犯(政府和社會文化)底線的勇氣,和挑戰何謂劇場「表演」的創見,都不容易在當代的香港劇場找到。近年以探索本地原創「紀錄劇場」為任務的「一條褲製作」獲藝術發展局資助致力朝這方面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其作品都是有意識地回應社會的創作,包括「菜園村事件」、「六七暴動」等。但在資訊海量的時代,劇場創作要在演出前和後在公眾間(而不只是劇場觀眾)引起漣漪是絕不容易;而批評力度亦往往失諸於尋找觀眾共鳴和提供「多元角度」的森林裡。
長年在香港推動劇場評論的「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亦組織許多國際交流,此為其一,由該會策畫及統籌的「雙城開評:滬港藝評深度交流計劃」(2018)。
《重建菜園村》觀眾Cici的網上評論,經常被劇團在不同場合引用:「選擇用藝術作為歷史、社區、群體的發展紀錄,並不是因為我們對於消逝的事物過分執著,而是因為我們看到這些消逝的事物中珍藏著的重要的價值。我們把這些重要的事物整理、組合,以溫和的方式向大眾訴說,希望能構建溝通、理解、支持,乃至傳承。」文中強調「溫和的方式」相當有趣,一方面說明了觀眾對劇場的想像與期望;另一方面在如此媒體生態下,即使劇場不規避「政治」與「議題」,但「溫和」是否更有效率地消弭掉劇場公共領域的創造力?有十二年歷史的藝評節目《演藝風流》在二零一八年全面退場,香港電台作為公營電台,對廣播空間內保持一定比例藝文與評鑑節目的責任更形消失;同時,演出量大增、觀眾的分眾越見微細,創作要凝聚討論的焦點相當困難。面對媒體被萎縮的現實,藝評(人)對「溫和」的策略是予以欣賞或是批判,這些討論甚至是消失的。
二零一八年熄燈,製作逾十年的藝評節目,「演藝風流」現場。
創作(人)和藝評(人)如何介入公共領域,重新創建「被看見」的可能性,在這個「人人參與」的「去中心化」年代更值得思考。莊梅岩為紀念「六四」三十周年創作的《5月35日》,她在謝幕時公開說到受到騷擾,創作與言論受壓近在咫尺;網路臉書多有分享,媒體只有和創作人跟進,但深度評論的關注與後續探索,卻好像未見出現。藝評人不是要把所有作品作對號入座式的社會或政治聯想,但如何梳理作品所關注的議題的公共性及其美學策略,將之置放在香港如今的脈絡中對照和評鑑,並在本地甚至是國際的(線上和線下)平台進行討論,似乎是更要做的事。經歷過二零一九年還在進行中的逆權運動,香港的現實比舞台更有戲劇性;有演藝學院的同學去年底罷演畢業作可以理解,但「不演」的另一策略,創作人是否更需要想像力和勇氣,以「溫和以外」的方式迎向這一波的挑戰,讓劇場創作體現其作為公共領域的功能;同時,我又想到梁文道那個未竟之行為從未過時,這張其實可以很重的影印紙,亦其實永遠在藝評人手裡。
圖片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提供
(原載於2020年3月《劇場閱讀》)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