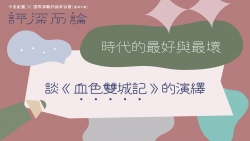 |
時代的最好與最壞:談《血色雙城記》的演繹
討論劇目:《血色雙城記》
藝評人:時惠文、李博文
主持:陳國慧
初稿整理:江祈穎
定稿:時惠文、李博文
英國文豪狄更斯舉世知名的文學巨著《雙城記》,以18世紀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當中講述基層與貴族之間的仇恨所引發的悲劇。英國劇場工作者何樂為(Jonathan Holloway)將之改編成《A Tale of Two Cities: Blood for Blood》,繼2016年香港及英國愛丁堡國際藝穗節(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巡演英文版本後,中英劇團在2022-2023劇季首度演出《血色雙城記》粵語版本,由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張可堅翻譯及執導。演出在原著的情節上作了頗大程度的改動,運用簡約寫實的風格去演繹這部作品,展示人性的多面。今次,請來藝評人時惠文及李博文,以及主持陳國慧,就文本改編、演繹手法、舞台調度、象徵意義等範疇,深刻探討這次演出。
(一)文本演繹:雙線敍事
今次演出特別之處,在於開場時已安排重要角色——盧斯因.文歷醫生(張可堅飾)出現在舞台空間上最重要的中間位置。這種特別的存在方式,令故事有更多不同的演繹。時惠文覺得這安排很特別,因為她一進場就看到穿着白袍的張可堅坐在舞台的中央,猜想他會是個很關鍵的角色。醫生在原著擔當着相連兩個城市的重要人物,很多故事也圍繞着醫生發生,所以特別期待看到這個角色的變化,例如坐監歷時18年前後。但後來發現演出並無對醫生作出個別描寫,彷彿幽靈般存在劇中,見證着整件事的發生,同時又控制着整件事。她見到張可堅作為藝術總監,演出醫生這重要的角色又同時在舞台上控制整件事,感到意義上有雙重意味,是一個有趣又有象徵意義的設計。
改編文學巨著需要作出取捨,李博文認為何樂為改編《血色雙城記》的重點,是以回憶切入的雙線敘事。是次改編內容講述在革命裡有很多不同的受害者,但受害者並不是全然邪惡的。何樂為選擇利用雙主角作雙線敘事。第一個主角——契尼.卡頓是一個受盡上司壓榨的中產階層,在社會上是一個受害者。契尼對奴詩.文歷一見鍾情,最後更犧牲自己的性命去成全奴詩和她的丈夫。而另一位主角也是社會的受害者——狄法芝太太,她的獨子被侯爵的馬車撞死,侯爵不但不作賠償,更推卸責任。從此狄法芝太太結下對權貴的憎恨,後來她把對侯爵的仇恨,報復於其姪兒查爾士.丹尼上,在共和國的法庭上控告查爾士,令他被判死刑,是一條復仇的路線。
(二)大時代下,人的選擇
在劇中,狄法芝太太和契尼分別被極恨與極愛完全吞噬,形成雙重主角的強烈對比。時惠文發現自己起初會同情狄法芝太太的遭遇,但往後對她的同理心漸漸減弱,反之對契尼這一角的感情越來越強烈,連繫亦更深。這令她記起導演曾經提過:表達愛是今次改編的重要訊息。
李博文認為原著《雙城記》側寫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描寫了人如何受到革命影響。而今次的改編選擇去時代化,把焦點放在人性之上,更加集中於角色面對不公時,會堅持善良,選擇寬恕去化解仇恨?還是選擇以牙還牙地報復,令仇恨不斷延續下去?今次改編的狄法芝太太由原著中親姊妹被侯爵性侵,改成兒子被侯爵輾斃,事件改動令仇恨侯爵的原因更私人化,由狄法芝太太對整個權貴階級的仇恨,變成對侯爵家庭害死兒子的血仇,要侯爵絕子絕孫,淡化了針對整個權貴階級的報復意義。時惠文認同加強了狄法芝太太的個人仇恨,反而會令觀眾質疑她作為革命領導人,推動革命背後的動機,未必真心想推動社會進步,而是為了一己私慾。
陳國慧則認為《血色雙城記》改編處理偏向強調人性的軟弱,強調人在社會下如何選擇,但同時亦弱化了時代背景,令她思考作品應否強調人性多於時代。時惠文指編劇何樂為也認為這二百年前的歷史背景在作品中並不太重要,因為我們永遠也可以連繫到「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個命題。
(三)演繹簡約而富象徵意義
將大時代放進小劇場,這極簡化的實驗是一個充滿野心和驚喜的嘗試。時惠文認為當中運用了約一百張椅子和鞋鋪滿方形舞台,象徵着革命中消失了的人,是一個具震撼力的舞台設計。當中椅子、鞋和麥克風這些物件擁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可見今次演出注重每個細節。陳國慧認為刻意運用小空間去說大時代故事,是一個美學上的選擇,帶給觀眾視覺上的另類體驗。
李博文指椅子和鞋象徵着在革命下的受害者,他們已非存在於舞台上,甚至世界上的人,而且整個演出演員一直都在台面上沒有離開過,在角色轉換時,將戲服掛在椅背上,這個演繹方式令人聯想到舞台就是一個大型監獄,所有人也被困在大時代中,不能逃脫。另外,他從劇中懸空的椅子,聯想到契尼要上斷頭台的情節,他認為椅子就像懸掛在空中的一把刀,針對着劇中的所有人,令他對此劇的情節有更多想象。
(四)強調雙重性的構作
李博文指出《血色雙城記》改編上想發掘更多人性的光明與黑暗面,所以透過一些重要角色,帶出他們同時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的雙重性。例如特別安排劉仲軒同時擔任契尼和侯爵這兩個角色,突顯施害與受害雙重性演繹;陳琳欣則同時擔任奴詩和巴撒,雖然分別是上流人仕與低下階層,但其實兩個角色較相類似,同為受害者,其親人亦被判罪,亦沒有以報仇來行動。
時惠文認為《血色雙城記》對比原著,沒有那麼工整去呈現對照這個特點,反而傾向打破傳統,契尼和侯爵的雙重演繹是一個很好的處理。劇中除了飾演醫生和狄法芝太太的演員外,其他演員也需要每人擔當兩至三個角色,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奴詩。但這個處理對於不太熟悉原著《雙城記》的觀眾是具挑戰性的,觀眾較困難去梳理主線以外其他角色之間的關係,亦難以理解故事推進。
李博文指出在開場之初,以演員旁述交代故事背景的處理比較混亂,旁白身分不夠清晰,導致之後進出情景和旁白交接不順,旁白內容難以分辨其可靠性,令觀眾難以入戲。陳國慧提到觀眾對原著的熟悉度亦會影響他們對演出的期望,這次演員需要同時處理兩個不同階層的角色,儘管演員已運用身體、 聲調和服裝去演繹不同的角色,但她發現角色間的階級分別不太明顯,在語匯上亦都未見兩個階級的明顯分別。
另外,李博文觀察到全劇只有七個演員去處理十三個角色,劇中嘗試運用定格去作場景轉換,而場景的轉換大部分集中在台側,演員們會利用設有燈光的麥克風表演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幫助場景轉換。這些安排維持了整個表演的能量和推進,但他認為無伴奏合唱的風格並不是最適合此劇的選擇。陳國慧認同無伴奏合唱的風格與此劇並不配合,覺得風格比較跳脫。時惠文亦明白場景轉換需要作出自然調動,雖然演出當中有變化,但也認為音樂設計略嫌重複。整體上,今次的演出將故事、場景、時間濃縮和簡約化的難度甚高,但卻能一氣呵成地處理,讓觀眾能夠感受故事和創作人要帶出的訊息。
(五)總結
整體而言,李博文欣賞《血色雙城記》在改編構作上的雙重性,何樂為作為此劇2016版本的編劇、導演和燈光設計師,同時也是2016版本的演員,參與劇中表演的部分,是完全屬於何樂為個人的《雙城記》。他取捨的決定明顯,亦安排自己在舞台上表演,這其實也在實行當中的雙重性。今次張可堅代替了他的位置,好像代入了醫生的角色去觀望整件事情,作為一個扣連了戲劇和現實世界的符號。陳國慧認同這個作品注入了創作人的想法,透過構作安排、不同剪裁和意象處理,令作品能夠繼續和觀眾對話,這絕對是值得我們繼續支持,能令作品的生命力得以延續。最後時惠文感嘆這次改編的作品中,演員需要身兼多角和表演空間的壓縮,正正反映了香港劇場現時的困難狀況,希望大家也能多多支持香港劇場。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