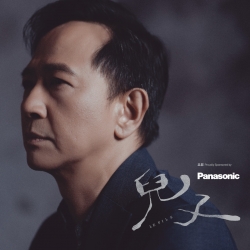《兒子》(The Son,2018)是霍理安・齊勒(Florian Zeller)家庭悲劇三部曲的終章,承接《母親》(2010)與《父親》(2012)對家庭裂隙的持續剖析,此劇以冷冽且細膩的筆觸聚焦於青春期的精神困境與家庭倫理的破裂。齊勒以節制的場景安排與精確的對話節奏將故事推入一種近乎臨床的觀照模式,讓劇場成為檢視親子互動、責任轉移與代際創傷的實驗場。戲劇不提供簡單答案,反而在多重沉默與未說之語中保留張力,迫使觀眾在不安與同情之間承受判斷與反思的重量。
香港話劇團於2025年9月27日至10月12日在香港大會堂劇院上演《兒子》,在文本移植、表演詮釋與舞台語彙的實踐上,呈現出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作品在本地語境中的可讀性,也削弱了原作欲提出的倫理與存在論張力。齊勒的原作以語言的斷裂、沉默的重量與關係間的聆聽失衡為核心,其戲劇能量來自於日常瑣碎中逐步顯現的證據與互為回應的節律。本場演出在若干關鍵場域的操作上出現失配,使得原文本應有的多聲部倫理問題被簡化為個體情緒的外顯,而非在舞台上被作為互動過程加以展開與檢驗。
在地化處理失當
將Nicolas的學業背景改為香港中學文憑試(DSE)(註:字幕為「DSE」,演員唸白為「高考」),表面上是一種合理的在地化嘗試,但此一改編未能同步處理或替換原作所依賴的文化象徵,因而造成符號與語境的脫節。齊勒原文本中「獵槍」段落在法國語境裡可指涉世代傳承、男性氣質或潛在暴力,作為象徵它在語義上具有多重回響;然而在香港,槍械屬高度管制的物件,打獵並非普遍文化經驗,該意象難以喚起觀眾的共感,反而顯得突兀且不合情理。當劇中把獵槍作為自殺工具交代時,這種符號上的不協調削弱了劇情的可信度與倫理張力,讓關鍵情節失去原本可被觀眾解讀與檢驗的象徵意義。
要使在地化具有效力,改編必須在保留原作象徵層次的同時,找到能在本地文化中產生等效回響的替代符號。否則,既非徹底本地化,也未能保留齊勒文本的象徵能量,改編結果反而形成語境上的矛盾。若採取更謹慎的語義再造或直接保留原有意象並透過舞台語彙加以說明,或許更能維持文本的倫理深度與敘事說服力。
情緒呈現先行,弱化人物關係
本場的表演取向偏向情緒直觀的呈現,卻因此弱化了原作所倚重的關係動力。齊勒文本的張力來自人物之間微妙的力場:話語的間隙、視線的轉移、身體距離的微調,以及在日常瑣屑中逐步累積出的證據。這些細微變化構成父子間情感拉鋸與溝通失效的邏輯,使衝突看似必然而非偶發。相對地,本場演員多以情緒基調作為角色標記,將內在狀態直接外顯,忽略了關係動機的漸進累積與彼此作用的變化,導致演員各自沉浸於自身情緒而缺乏互動上的張力與連結。
在角色細節的處理上,職業、社會身份與語言節奏的契合度亦有所欠缺。父親Pierre身為律師的設定本應在語言結構、論述方式與聆聽策略上留下痕跡,然而表演傾向以單調且高能量的語速呈現,反而強化了「會說但不聽」的刻板印象。
兒子Nicolas的處理則落入將複雜內在狀態精神病化的陷阱;他既渴望被救援又難見希望,這種內在的拉扯卻被簡化為病態符號,導致角色動能在開場即被固化,戲劇的因果與張力提前耗盡,舞台從「說明為何變成如此」退化為「展示已定型的情緒」。
場景關係的處理亦出現失衡。Pierre與前妻Anne的冷淡對話難以讓觀眾感受到曾經存在的情感重量。而現任妻子Sofia的登場本應引入新的情緒張力,卻被刻畫成對前妻Anne的劇烈戒備;這種「前妻無害,現妻卻如臨大敵」的設定,讓整個場景陷入一種不協調的情感錯位,亦使本應微妙的三角關係走向俗套。結果是衝突雖然爆發,缺乏先前情感與動機的有機累積,後續的對抗只有被劇情推動的高潮,而非從關係發展必然流出之結果。角色間的情緒鋪陳略顯突兀,未能有效傳達人物的心理層次,反而讓場景變得像是「前妻不可愛,現妻醋海翻」的情緒鬧劇,失去了原本應有的深度與節制。
舞台設計焦點偏離劇作動力
本場舞台以黑白灰的極簡調性構築出一種冷冽的視覺場域:灰白背景牆、黑色沙發與簡約燈具共同形成一個去個人化的日常空間。隨劇情推進,佈景被逐步剝離,最終近乎空無,這一設計語彙明確指向「缺失」與「虛無」的意象,表面上看似契合Nicolas的內心狀態,但在實際的敘事運作中卻產生了語義錯位。當舞台本身成為空洞的符號時,觀眾的凝視被自然引向空白而非角色間的張力,使得設計的焦點偏離了劇作真正的動力──父親心理的變化與其對關係的施加。
空間的簡化在理論上可放大情緒的聚焦,但在這次演出中,空白反而扼殺了關係記憶的痕跡。舞台並未因父親的職業、期待或行動而獲得指標性意義;相反地,空蕩的台面像是一張等待被填補的白紙,將「缺席」等同於「兒子的虛無」,卻忽略了父親作為施加期待者與行動者的具體存在。由此產生的視覺權力關係,讓觀眾在視覺上優先感受兒子的失落,而非經歷父親期待破碎時那種逐步耗損的權力與孤獨。
此種漸變式的去物化處理與話劇團2017年《父親》的舞台策略存在明顯血脈相承,但在文本需求不同的情況下,重複相似語彙則成為問題。《父親》中舞台的抽離或許服務於主人公記憶與身份的瓦解;然而《兒子》作為三部曲的終章,其核心在於倫理責任的轉移與聆聽失衡,單純複製先前的視覺手法,未能提出對父子關係新的舞台化詮釋,反而削弱了終章應有的獨立張力與詮釋深度。
此外,燈光更多作為冷色氛圍的平面渲染,而非情緒節律或注意力轉移的工具。演員在場域中的移動也多呈定點或線性,未能透過身體關係的接近與退離來呈現權力、關懷或疏離的微妙變化,這些未被開發的要素本可使父親的期望、失落和孤獨在舞台上具現化,而非只停留於台詞之中。
筆者認為,若以父親的主體性作為視覺敘事的中心之一,舞台設計則能更有力地回應文本,讓空白不再單一指向虛無,而成為父親內在崩解的層疊,將抽象的「期待落空」具體化,讓觀眾體會父親的失落與孤獨,而非僅在語言層面被告知。
導演的選擇
導演對文本的選擇顯示出若干值得商榷的取向。齊勒在《兒子》與《父親》中以「誰能發聲、誰被忽略」來構築倫理場域,文本的力量來自多聲部之間的張力與互相制衡。當導演將焦點過度集中於個別角色或追求單一的形式美學時,原本的多重對話便容易被遮蔽。何時讓話語斷裂、何時讓沉默說話、場上人在被聽見或未被聽見時如何回應,這些關係性的微動必須被系統性地累積與呈現,才能使舞台成為倫理問題的試驗場。
演出中顯現「情緒瞬間」佔優而非關係動作的漸進累積。演員以強烈的情緒基調標記角色,雖能短時間內引發戲劇效果,卻使衝突看似突發而非從關係發展中必然流出。當表演缺乏前因後果的連貫性,倫理辯證便無從在觀眾心中建立:觀眾感受到的是情緒的爆發,而非「為何會爆發」的理路與責任分布,角色因此淪為情緒的符號而非活生的他者。
香港社會對學業成就與家庭期望具有高度敏感性,父親對學業的強烈責備引發現場明顯的身體與情緒反應,觀眾帶著在地倫理想像進入劇場。這些即時反應表明潛在的共鳴與批判基礎,但演出並未提供足夠的語篇架構或結構線索,引導這些情緒向更深的倫理反思延伸。結果是觀眾停留在感受層次,缺乏被引導進行結構性判斷或重新定位自我與他者關係的機會。
情緒張力與視覺一致,惟跨文化轉譯過程見缺失
香港話劇團的《兒子》在若干片段展現出強烈的情緒張力與視覺一致性,惟在文本語境的連貫性、表演關係的層層累積、舞台語彙的證據性建構,以及凝視/被凝視循環的具象化處理上仍顯不足。演出未能充分轉化齊勒文本中對「聆聽」、「責任」與「他者之目光如何構成個體存在」等倫理命題的哲學探問,而傾向將其簡化為情緒的表層展示,使得原本深刻的哲學意涵未能轉化為可供觀眾檢驗與感知的劇場經驗。
此一缺失並非僅止於技術層面的瑕疵,而是牽涉到劇場在跨文化轉譯過程中如何重構象徵語義與關係敘事,使觀眾得以在具體的舞台事件中完成意義的再生。唯有如此,劇場方能真正承載文本的倫理重量,並回應其所提出的存在性挑戰。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