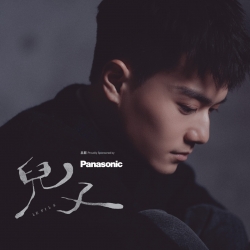這到底是一齣法國作品、英語區作品,抑或是本地的作品?怎麼看起來連一點間距感都沒有,彷彿就是當下這個城巿的寫照?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數字顯示,過去五年有131名學童自殺,中學生佔九成。去年有2,090名中學生患有抑鬱症、焦慮症等精神疾病,較五年前的820人,增加一倍半[1]。《兒子》所呈現的家庭實況,我們沒有辦法迴避,因為我們總能找到其中一個家庭崗位代入其中,而最「虐心」[2]的是,那些近乎是日常的對話,最終居然促成一條人命的終結。
本戲由Pierre(余翰廷飾)向前妻既綿密而不安的質問開始,揭發兒子每天背着書包出門,卻始終逃避上學的事實。在這短短的兩分鐘裏,令觀眾懷疑這個原生家庭的背景,以及父母的個人性格,或許促成了兒子的精神疾病,而最終成為兒子走上絕路的兇手。如果是這樣,這個戲未免太俗套,也過分簡化角色的處境,而最終難以引起大眾對於這種問題的關注。
隨着戲的開展,余的說話方式並不單調平板,時而理性,時而溫婉,時而權威,時而風趣,倘若兒子後來不是當面辱罵他,他總是能展現他的理性持平,發而中節的特點。直到兒子忽然向爸爸直訴胸臆,指「生活擔子太重」,和媽媽相處得痛苦難耐,要求和爸爸一起生活,觀眾的關注點正式轉向兩位媽媽和新的家庭生活,繼續尋求其他「疑點」和「被告」。
無論場景怎樣變換,台上都擺放着同一套梳化,如果是在家裏,梳化呈曲尺型,反映家人珍視對話的特點;如果是在醫院,則呈直線型,儘管醫生多番要求大家坐下詳談,卻始終無法「對話」。導演的處理殊堪玩味,傢俱理應反映了角色的願望,爸爸也的確在這張梳化上和兒子展開一場又一場的對話,只是這些對話很多時候演變成質問和答辨,對話展開了,但溝通失敗了,事不遂人願。溝而不通的例子,也發生在醫院那兩場戲。醫院的等候廳本來就不是讓人交談的,可是醫生本着良好意願,希望遊說家屬讓兒子Nicholas留院。直線型的台位,其實很難擺的,有時甚至擺出媽媽坐下,爸爸站立和醫生對話的台位,以緩和直線平排台位的僵硬感。他們都關注兒子的病情,他們都需要對方的幫忙和合作,可是在留院接受治療這一點上,最終卻無法取得互信和共識。傢俱的擺放配合慘白的光管燈光,都彷彿和劇情互相注解。
戲中,兒子初到新的家庭,偶現情緒失控,甚至翻檯翻櫈,令觀眾確立對他的病情的理解。為甚麼需要「確立」?此處筆者對「兒子」(羅文澤飾)的演繹方法有一點不滿足。羅氏選擇了言語能力略遜、對人際關係和社交有鈍感,甚至附帶些微智力缺陷的演法。這種設定在現實上是有可能,也是滿普遍的。可是,這個角色不但講得出「生活很重」的話,平時和各人的交流都「有文有路」,甚至經常關懷到別人的心理需要。有一次他在向爸爸的新妻子Sofia質問,有沒有設想過搶走自己爸爸有錯,隨後居然為自己的唐突失言而道歉,儼然一個成熟的紳士。他對於自己𠝹手、逃學、選擇跟隨父抑或母生活、選擇留院還是回家等等,都有清晰的想法和理據,而且能妥善表達出來。從劇本這些設置來看,兒子擁有高階思維、心思成熟細膩、觀察入微、語言靈巧的特點,只是高度敏感、情緒波動劇烈、容易扣連自身往事而產生負面想法,亦因抑鬱而慣以自傷行為調節感受。當然,後來因為事態激發他產生尋短念頭,那是後話。筆者並非否定目前羅氏的演法,也承認觀眾容易接受這種人出現在這種故事裏,只是想提出「若果不是這樣演」的假設,會不會較易將戲的焦點重新瞄準焦慮/抑鬱類病情,令大眾客觀關注這個現實,而不是沉溺在這個悲劇人物的遭遇上。
「兒子」偶發的翻檯行為後,導演的處理頗為耐人尋味。被翻轉的茶几就一直翻轉着,原本在茶几上的雜物,就這樣被四腳朝天的茶几砸住超過一場戲。為甚麼這個家裏的人都不打算整理一下呢?兒子和父親先後坐在翻轉的椅子上說話還可以理解,因為兒子是「有問題」的,而父親正在煩愁失意,或許沒有心思理會;可是茶几長期翻轉卻沒有處理,彷彿象徵「那些人」對「某些問題」視而不見。最諷刺的是,導演多次安排這家人拿着瓷杯餐具出來飲咖啡吃早餐,他們卻寧願把東西端在手上,或直接擺在地上,也不願意放好茶几。後來女主人更乾脆把茶几拉出家門扔掉了,這些奇怪的舉動和這個戲的現實風格極不諧協,令人不得不注意,相信是導演有意為之,站出來要向我們宣示戲的其中一個主題。以舞台這種藝術形式說故事,一般是全知視覺,若沒有大段獨白,一般難以讓角色自陳心迹。台詞最多反映角色理性的心理活動,卻無法透視他們精神層面的狀態。家居混亂,在現實角度,反映角色無暇兼顧整理;從虛筆的角度觀之,或許有效地反映他們當下焦慮、壓抑的心理狀態。無論如何,雖然筆者沒有強迫症,卻因此引起了一種焦躁的心情,這種心情主要還是一種不安情緒,至於共鳴和理解,還需依賴往後的情節。
說到不諧協,導演對幾個過場的處理可謂神來之筆。漫長的家事爭論是這個戲的肌理,雖然爭論的出發點都是善意的,但往往在各人的方向不一致時,令觀眾扼腕歎息,特別在預計到這樣發展會引向無底深淵時,更加萬分失望和焦躁。就在這個時候,導演好幾次奏起歌劇式的音樂烘托悲情,讓觀眾滋長情緒並壓抑着。當最後一句台詞講完,觀眾以為馬上就要暗燈可以呼一口氣、偷偷流一滴眼淚時,激昂的音樂卻忽然被切斷,燈光和場景旋即切入下一場,同時下一場戲又已經開始—剛才那口悶氣,要嚥回去;這場仗,又要打下去;這件事,還是被迫要從一個冷靜的角度,繼續關心下去。
《兒子》所建立的世界,其實並不冷漠,相反,每個角色都合理、包容、有愛。Pierre和前妻離婚,可是前妻有事,Pierre都願意協助,甚至將兒子的撫養責任,重新扛上身。Sofia口裏有微言,但仍嘗試和「兒子」好好相處。當期待已久的意大利之旅泡湯,看得出她極其失望,卻仍儘量理解和支持Pierre的決定。後來Pierre和Sofia爭吵不住,Sofia仍然選擇和平談判,並獨自帶嬰兒出門散心,臨別彼此都是和和氣氣,盼望回來時一切都好轉過來。張紫琪將Sofia這個處處忍讓,讓而不退,以大局(她的家)為重的被動角色,處理得自然合度,為《兒子》架設了第一層壓抑的調子。前妻Anne是這個故事的第一受害人,可是她為母則強,即使兒子Nicolas出走父家寄居,Anne仍然抵住孤單淒涼,認為只要對兒子有好處便願意接受。醫護亦沒有被醜化,雖然Nicolas想出院時把醫院描述成鬼域,令觀眾一度懷疑醫院是否可信,但後來大家都明白,醫生是本着專業判斷,誠心照料每一個病人。總之,Nicolas並不是生活在一個典型的破碎家庭,即使傷痛難癒,父母都沒有完全離棄他,經濟條件也還可以,到底誰對誰錯呢?不如換個角度,《兒子》壓根兒沒有找尋兇手的想法,正因為所有人(包括Nicolas)都合情合理,看戲後的餘韻,自然縈繞着「病」本身,而久久不能釋懷,是宿命還是選擇,看倌自行判斷。
聽聞看完戲的人,紛紛向人分享着自己身邊和「病人」相處的經歷,說明觀眾都受到了震動,開始關注身旁的「患者」,甚至「未患者」,而不只是沉淪在故事本身。倘若屬實,誠然是《兒子》的大成功!
[1] 根據有線新聞,〈過去5年逾百名學童自殺 9成為中學生 患抑鬱症〉,2025年4月3日報道(https://www.i-cable.com/新聞資訊/334972/過去5年逾百名學童自殺-9成為中學生-患抑鬱症?utm_source=icable-web&utm_medium=referral)
[2] 本劇的宣傳品用語。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