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歌仔戲才是唯一發源台灣、最能彰顯台灣本土文化特色的地方劇種,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京劇卻是台灣最特別的傳統藝術。港人也愛京劇,但此愛絕非彼愛。試想香港政府若出資公辦一家京劇團,既有全套人馬,又有專用劇場,更時時代表香港四處巡演,會怎樣?從文化上來說,京劇,其實就是台灣人的鄉愁。「國光劇團」之所以存在,離不開這份鄉愁;而為紀念民國百年而作的《百年戲樓》,與其說是嘆京劇伶人的「百年身世」,不若說是寫台灣文化的百年鄉愁。
故事從白鳳樓對嚴四鳳的取代講起,用趙雪君(編劇之一)的話來說,這段講的是「愛與理想」。於是我們看到,嚴四鳳死了,所有舊戲班裡的齷齪也跟著死了,取而代之的白鳳樓用非同尋常的「愛與理想」,將「鳴鳳班」經營得比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大學還溫暖——說經營,其實並不恰當,因為這位新班主從不憂柴憂米,心裡只想著怎麼培養那個既不好學,又不聽話,也不友善的年輕男旦小雲仙,不僅為他定製繡鞋,半夜陪他練功、談心,將自己當年忍辱含垢才學來的絕活毫無條件地傾囊相授,更為他堂會求饒、捱罵、捱打。好一腔全心全意、不求回報的愛!難怪師母後來面對背叛師門而去的華雲(小雲仙改生行後的藝名),哀哀質問:「嚴四鳳欺負他,他待你可不欺心啊!你甚麼都帶走了,只留下他送你的那雙繡鞋,可真傷人啊!」
很明顯,作品想以白鳳樓和小雲仙(華雲)為縮影,寄託一代京劇人為藝術尊嚴的抗爭、對傳承創新的思考。衆所周知,京劇在民國時期曾有過絕代風華,但藝術的巔峰並不代表人性的巔峰。拋開舊戲班時代的種種血淚不說,哪一個行當挑班,決定了舊戲班內所有的生存邏輯和人物關係,「鳴鳳班」誰掛頭牌?正值舞台盛年的知名老生,買下戲班後為甚麼只一門心思捧一個年輕男旦?儘管懷著「死過一回」、「連說都不容易」的屈辱,白鳳樓也當然可以善,但嚴四鳳的惡難道就是與成長背景無關的、天生的、個體的惡?為甚麼白鳳樓與他不同?又為甚麼白鳳樓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白鳳樓的行為邏輯直接影響著他的形象是否成立,也影響著他與小雲仙這段故事的藝術真實。人是附著在歷史之上的,所謂一代之縮影,更不能超脫歷史的真實邏輯,將所有人物、情節放諸於真空之內,否則無論承載多麼偉大的「愛與理想」,都只是臆想和空談。在白鳳樓與小雲仙的故事中,精心編織的溫情面紗遮蔽了歷史的複雜與醜陋,同時,也遮蔽了情感的層次與真實。
藝術創作要想動人,不是看你夠不夠煽情,而是看你有沒有不溢美、不隱惡的真誠。在這一點上,主創們的「民國懷戀」或說「文化鄉愁」,顯然影響了前半場的藝術判斷和取捨,致使人物性格與情節邏輯混亂、失真。相反,在後半場華崢與茹月涵之間「愛與悔恨」的故事裡,未親身經歷過大陸「文革」的主創們以他者的敘述角度,既在情感上恢復了冷靜,也在藝術上保持了中正、客觀,同時,由於大陸與台灣在那個歷史階段政治運動的某種同步性,更加入了一些同理心,使得整個舞台呈現豐富動人起來。
尤其是茹月涵背叛華崢的一場戲,處理得既殘酷又浪漫。紅衛小兵們身著前半身黏貼上去的制服,誇張而不失舞台美感。審問茹月涵的幾個紅衛兵皆由小花臉扮演,很符合人物身分。高舉紅燈的李鐵梅鏗鏘高歌,與小花臉漫畫式的審問穿插推進,營造出整個環境的荒誕意味。「蟠龍繞鳳金絲掐紅牡丹重瓣小繡鞋」的名字被迫在茹月涵的口中反覆吐納,將人物步步緊迫的心理節奏外化出來,使之後的崩潰與含淚控訴如同決堤洪水一樣既令人震撼又全在觀眾情感預期之內。而當認罪的華崢被兒子華長峰接回家後,那一段「用手兒撥開紅羅帳,嚇得我三魂七魄颺」的四平調,更將「到底是我看錯了你,還是你看錯了我」的悽惶與絕望,演繹得貼切真摯。
《百年戲樓》的創作源自以「國光」藝術總監王安祈、導演李小平為代表的一批台灣京劇人對藝術前賢的想象、對昔日熱鬧的勾描,以及對今日堅守的訴說。「文化鄉愁」的另一面,其實是對自己「根文化」的挑選、把握與守望。從《三個人兒兩盞燈》、《金鎖記》、《水袖與胭脂》……甚至《狐仙故事》,再到非京劇的「京典舞台劇」《百年戲樓》,「國光」一直在沒有地緣優勢的條件下,努力將現代人共通的情感注入傳統,開創著屬於台灣的當代京劇的風格與路向。儘管創作有時成敗,但「七成是青年觀眾」的成果卻令人看到台灣京劇的明天,也向所有思考傳統藝術發展的有心人證明,成功的「定位」藝術,有時比成功的「創作」藝術,更容易影響一門藝術在區域內的發展。而這,恰恰是「國光」每部作品所能帶給我們的最佳啟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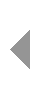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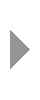




《百年戲樓》
演出團體:國光劇團(台灣)
評論場次:2013 年 11 月 17 日,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作者簡介:戲劇文學專業出身,寫劇本,搞研究,做電視策劃,當文化記者,十幾年沒離開過一個「戲」字。評戲,是專業,也是生活。
照片提供:國光劇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