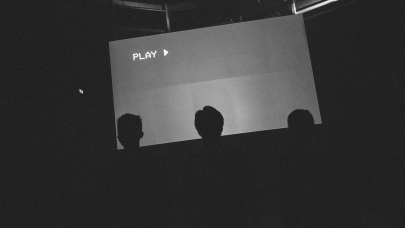無以名狀,無法言傳,無法被理解的感受,在舞台上由表演者傳達,然後化成於觀眾席與舞台之間的共鳴。一同經歷,一同感受,無形卻真實的交流在舞台上、在舞台與觀眾席間發生。也許我們仍然可以相信,這種交流依舊能讓生命互相影響,以至有改變的可能。
這是我喜歡劇場的原因。
也是這個原因,寫作的時候,我總是以極其個人的角度出發的,生命上的經歷,生活上的遭遇,都是我創作的源頭。感性的,情緒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個人的,狹隘的。然而,劇場一直提醒我,人無法與社會切割,就算再個人的故事,也與環境、社會、世界有所關連。逐漸逐漸,我所追求的一個文本,以至於一場戲所需要帶出的,是人與自我的關係、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多重而又互相扣連的關係網。縱然不一定成功,但確實是希望能把個人扣連到社會多一點,讓個人的事情不那麼個人,也讓社會的事件不那麼遙遠。
回溯自身的記憶,對於社會變遷的印象,始於十歲的那年。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電視螢幕直播香港回歸的交接儀式,旗落,旗升,一些人離開,一些人到來,那時候像是看著一個遙遠國度的新聞片段。孩童的我只覺得無關痛癢,無從將這片段與自己的生活聯繫,無法理解到那是香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這是我對「歷史事件」的最早記憶,一種旁觀者的記憶,一種置身事外的記憶。
《被動式 Passive Voice》劇照
九七往後的,也許是年歲的成長,也許是問題的逼切,也許是種種的不公,從隔岸觀火到埋身肉搏,讓人無法繼續旁觀。二零一二年,走在反國教的遊行路線中,人潮的聲音與空氣的震動,一路上無數群眾的願景、理念、想望,或沉默或響亮的在現場交滙,是攝影機無法呈現的無形之物,是認知的理解,同時是最直觀的感受。數年後,數十萬人在馬路上駐足,用時間,用心力,用血和汗表達對這城的關心,對改變現狀的渴求,卻仍然不得要領,反而每況愈下,讓人不得不對這地方的未來感到悲觀。
矛盾的是,越是困頓的現實,往往亦是最好的原動力與素材,無數創作者嘗試在劇場中尋找出路,渴望在一片灰矇之中挖掘出陽光。我始終相信,精彩的故事不一定有大團圓結局,不一定有燦爛的明天,而是當中的主人公鍥而不捨地追尋所渴求的事物,縱然歷盡艱辛,歷盡苦難也所在不惜。對未來茫然的時候,就先往回看,看從前的人如何面對,如何走下去。不知道走向何方的時候,就去看看我們從何而來。這個城市仍然有許多過去可以梳理,許多的未來需要思考,面對種種讓人氣餒的現實時,唯有繼續行動,繼續尋找,才能有一絲機會尋覓到更多可能,才能更接近我們所想望的理想。
在這個冷漠又撕裂的時代,劇場需要呈現更多不同的人物,讓人可以理解更多的「他者」,為甚麼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場景,為甚麼對立,為甚麼同行,讓我們能嘗試明白對方多一點。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人物同時在舞台上展現自己的觀點、欲望、快樂與哀愁。讓我們能感受他人的傷痛、進入他人的角度,讓人們對彼此的了解多一點。劇場可以呈現歷史、心靈的傷痛、渴求的理想,它可以重提一些人們易於遺忘,甚至已經遺忘的東西。六七暴動、中英談判、八九民運、九七回歸、沙士、反國教、保護菜園村、雨傘運動,可以是新聞片段,可以是歷史,可以只是一個名詞,但在劇場之中,它們也可以成為一個個獨特生命的故事,重新提醒我們跟他們的連繫。
即使在種種限制之下,我仍然相信,我們還是需要做好我們可以做好的事情,例如,說一個有意義的故事。也許最終仍無法改變世界的運轉、社會的變遷,但至少我們可以說我們所關心的,一些在官方、在標準答案以外的故事,被遺忘的人、被淹沒的聲音、被塗改的相片,通通可以在劇場裡重新挖掘,透過表演者的身體重新活過來,讓他們仍然被記住,仍然被傳承。
只要你,只要我們願意的話。
照片拍攝:Hui Hong Nin
作者簡介:自由身劇場工作者,畢業於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系,後負笈臺灣,2012年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表演藝術研究班,主修跨領域表演、跨文化劇場、劇場美學。2013年創立眾聲喧嘩,現為其核心成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