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6年年底參加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在羅馬尼亞舉行的青年劇評人工作坊。工作坊在羅馬尼亞第二大城市Cluj舉行,附屬於Cluj舉辦的國際戲劇節Interference。工作坊前後約一周。我們晚上看戲,第二日的白天聚集在主辦方安排的咖啡館裡面的小室,進行圓桌式討論,主持人是來自倫敦的評論人Diana Martin Damian。本文記錄我參加此工作坊的所感所得,主要是關於評論的思考,與走在演藝評論路上的諸君共享。
進入正文之前,我必須在文章開頭交代我的背景,便於讀者了解我的坐標和角度,以及我天然的局限。
2012年以素人方式投稿「藝Po」,這是我劇評寫作的起點。我的大學本科及碩士都是修讀社會科學,與戲劇甚至藝術基本沒有沾邊。因我學術訓練的緣故,我對社會性議題、歷史和現象及社會科學理論相對敏感,但對戲劇理論或文藝批評的知識則幾乎為零。過去的四年裡面,參加了好些不同形式的評論寫作工作坊,由新手慢慢進階,持續但不算頻繁地寫作劇評並發表,以非學院的方式慢慢積累起對於(香港)劇場的了解,漸漸受邀寫文、駐節評論、到參加研討會,從不同切面在體驗著評論為何事。至目前而言,我會界定自己為一個開始入門的評論人。
劇評人的模樣:個性盎然而獨立自由
此次的工作坊,對我來説,部分是認識和思考上的深化,部分則化作了身體經驗。化為身體經驗的首先是瞥見了來自歐洲和亞洲[1]的不同劇評人的模樣。我很喜歡此次遇見的這些劇評人們。他們形象鮮明,目光銳利,有獨立觀點。他們自由,充滿好奇,有個性。他們不怕異議或爭論。他們既是劇評人,也展露普通人的樣子。他們喝酒抽煙,他們談天說各自文化裡面禁忌的詞語,他們爭吵辯論握手擁抱。斯洛文尼亞劇評人Rok好動而沉穩,第二日一到達討論室便提議我們每日坐下的位置必須是之前未曾坐過的,而提起讓他難以忘懷的六小時的《海鷗》動情不已,幾近語塞。來自葡萄牙的劇評人Statt是舞者出身,手上戴著父親送她的結婚禮物,上刻希臘面具——一面是喜劇一面是悲劇;但她對傳統戲劇無感,認爲藝術就是娛樂,藝術不是思考、無關深度,而是享受和逃逸,堅持一個評論人必須要能給予讀者其他人無法給予的專業評論。摩爾多瓦劇評人Rusanda,親切又不介意離群,認真聽他人發言,遇到不明白的英文詞便直接問何解,當她聽到Statt關於藝術的判斷的時候,大聲說I don’t agree,拼命搖著頭響亮地重復數次,I don’t agree, I~don’t~a~gree。日本劇評人Tomoko很是好學,斯文矜持常帶笑容,和熱愛身體接觸的歐洲人保持著肢體距離,被歐洲參加者視作東方女性的模版;每當餐桌上祝酒說「Qsin Qsin」(西班牙語)時尷尬不已,因此發音在日語中是生殖器官的穢語,但是,在看了戲劇節中一齣叫她失望透頂、有負盛譽的演出之後,她竟憤慨到直説I can say Qsin-Qsin to this sh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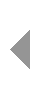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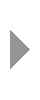



這便是我很喜歡他們的原因之一:他們自然散發出來的個性,和隱藏背後的獨立性。他們並非刻意,卻以自身言行展示給我看怎樣是一個獨立的評論人。在他們面前,你被教導和允許獨立。
像Statt和Rusanda關於藝術的不同立場,只是發生在工作坊中的爭論的九牛一毛。對於戲劇節中的某些有爭議的戲,有人喜歡,有人不喜,但彼此在爭論時毫無尷尬和不快。你清楚看見大家在交流的是觀察和判斷。我有時候忍不住將其與在香港的工作坊相比。在香港,更多聽到的是各自表述,而非真正算得上討論。一方面緣於參加者大多業餘,但經驗尚在其次,更加關鍵的,是各人的態度,及因各人態度無形凝合成的氛圍。
Rok被主持人Diana問到戲劇節其中一個戲的舞台形式是否有助其意旨表達時,他稍停一下,然後直接說,I don’t know。那一聲「我不知道」真極有力——如此的直接無蔽,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會勉強說出一點似有還無的評價,更不認為若直說不知就遜於他人。
我想,這也是獨立。西方人的個人主義或許有助力,但我更相信,在座都是一個個有獨立見解的評論人——獨立在此的意思是說,你直言所想所思,你不會因爲他人不同意或不接受你的觀點而有任何不快。各人性情當然未必完全契合,也沒有必要一定互相喜歡,但發表和討論時彼此共識到重要的是觀點與分析,交鋒的是不同立場之下的斷定。在那樣的氛圍之下,你不須關心論點和思考之外的事情,你無須分出心神去考慮這樣會否得罪或討好他人;在這過分的自由之下,你自己要為自己的觀點鋪磚蓋瓦。在這樣的工作坊裡面,如果你不獨立,你便難以有自己的位置。你必須為你自己的觀點辯護——你的觀點是你的,你要對其負責——展開、充分深入、抵擋質疑和挑戰。
某程度上,他們展示出來的,是評論人與自己的觀察、思考、判斷相處,而將其獨立、真誠地展現給他人,無論是同行、前輩、劇場工作者還是觀眾。這是評論人對內可以呈現的最好姿態——你便是自己判斷的標杆,你站立在你的評論的後面,你樹立自己,你樹立自己的評判和論證。
在做到寫出好的評論之前,必須先努力做一個獨立的評論人。
從新手到初階劇評人:視野
意識到視野對於一個評論人的必要性,是另一個重要收穫。當你離開本地,走出既定視點,視野的重要性便突顯。要想在評論的道路上繼續前行,必須要從一個僅僅執筆的人,延展成一個有視野的人。
「視野」並不是抽象的,而且必須要防止其流於空泛或淪為宣傳。具體來說,以客體言,視野是一種大背景,是現存境況所處其中的大脈絡;以主體言,它已經內化成須臾不離的參考框架,在看見一個事物的時候便可判斷它所處的位置、它與周遭環境的關係。
工作坊中,日本劇評人Tomoko有一次用「後現代」去討論劇作。Diana點評時帶過一句,「後現代」這個視角是九十年代的,現在已經過時了。我當時十分驚訝。一方面是這個判斷本身。「後現代」多少對我來説還算是個時髦詞彙,但原來在歐洲的眼睛裡頭它已經不在當下的視野。除此以外,更令我詫異的是Diana能夠這樣給出一個評論現狀的定性,這暗示她多麼清楚目前的批判傾向及文藝思潮。一個資深評論人就這樣不為意地做了「視野」為何物的示範。這種知道,並不止於讀懂「評論概論」一類的教科書文字,而是化作一種見——從「知」出發,到達「見」的層面。它最初以知識作爲基礎,但將逐漸如地質層般積澱起來,融入評論人自身的思辨框架。我當時反問自己,我寫作劇評也有一小段日子,我卻完全說不出香港的劇場評論處於哪個階段,有哪些大的思潮作為背景。是仍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下和批判對象之内嗎?是將藝術作為一種社會/政治批判?是屬於哪一個美學傳統呢?我通通回答不出。
這個小插曲是一個極大的提醒。它逼問我作為一個劇評人,是否知道評論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是否知道走到最前面的有哪些人,他們站在哪些巨人的肩膀上,他們在做甚麼試驗甚麼,他們推進的邊界是甚麼,擴寬的地平綫又有哪些。又或者,提醒走在前面的人們有意識且身體力行地跟我們這樣的後來者展開出一個更大的圖景,而不僅僅是一個演出、一個劇團、一個現象、一種生態。
以目前的我可以把握到的「視野」,首先是對世界的認識——這種認識,不是浮疏一瞥、含糊籠統、以偏概全,而是目明心清、橫貫連綿,往前說,可以深入到最前沿的處境,往後說,可以接續上傳統和脈絡。工作坊中,對比其他科班出身的評論人,我深感到自己對於經典劇目的不熟悉,像他們開玩笑時援引莎士比亞,我便處於一種自知的尷尬中,渾然無法分享其趣味。當然,是否可以用莎翁對白來開玩笑不過是表徵,要緊的是這戲劇傳統中的土壤養分是否可轉化成自身的根莖組織,成為有機一體,才在這種場合因內化而外顯,現出各人不同的風趣和魅力。
「視野」其次是對自己所在地的藝術/戲劇現狀的熟稔。隨著John Berger去年離世,類似這樣稱得上世界級的評論人將越發遠去,如林克歡在世紀之交所言[2]——二十世紀的戲劇版圖已是分崩離析,二十一世紀可預見將更加碎細,再也難以有一個所謂世界性的戲劇傳統出現。評論(及其力量)基本上便縮窄到國家的版圖甚至是城市的方圓。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劇評人首先,或者說更多都是在自己的城市區塊裡面發揮影響。在世界意義上的視野應廣博、連綿、充分,而在地意義上的視野,則講求細緻、敏銳、見解。前者有藝術史和近現代戲劇史作支撐,尚有不少公認的路標(名字、流派、風格等),而後者則極仰賴個人身處在變動不居的社會環境中的判斷和取捨,因此亦將是更大的功課。我想,由新手轉變成一個獨立評論人的衡量標準之一,是你是否有底氣建立起一個以你自己的框架、準則,審美和品味為基礎的在地視野。
舉一個例子。有一回我們談論到各自發表的媒介,我們在座不少仍然在傳統的報刊上發表。Diana稱她現在基本不會再幫某些大報寫劇評。英國大報的文藝副刊或欄目,裡面的劇場評論文章,大多有固定格式,先是演出哪些角色,用了什麼技巧,有甚麼特別之處,然後打分,「五星,推薦!」如此這般的套路。以Diana的分類,這也是評論,但屬於報道式的評論,落入新聞的傳統,她所概括的三個評論傳統之一。最早的是文藝批評傳統,它源遠流長,最早期的劇評多是沿用文學批評的路徑。這個傳統注重文本,用的是細的分析法,著眼是敘事、情節、張力、衝突等。其次是新聞傳統,是近兩百年內的事。有一說認為沒有記者不能寫的,戲劇當然不例外。這使得評論開始有其公共性,因為發表的媒介直接面向識字公眾。第三,也較近的,是劇場研究這個路徑,將評論收歸在戲劇的領域之中,將評論視為劇場的有機組成,用的是舞台、演員、導演等劇場詞彙學去分析評價作品。這是Diana針對英美戲劇評論追溯出來的三條源流,以其社會狀況、發表媒介和學科根源來劃分。這三個「傳統」,換了一個地域,例如香港,是否還適用?又或者,即使在英美語境下討論,是否毫無爭議?例如,記者撰寫的劇場評論,以報道而不以藝術作為出發點,是否還可以算作評論?反駁者如英國資深評論人Mark Brown就認為評論是處於新聞(journalism)與藝術之間的謹慎地帶,不是報道亦不是藝術[3]。
無論如何,可以說,視野既是既定,也是時移的。它提醒評論人要有更大的察覺來定位自己筆下的文字。
回到評論的本質,發散評論的可能
在此工作坊中我們除了看戲和討論,還做了幾次寫作練習。練習一是用二十分鐘寫一段描述(description),描述昨日看過的其中一齣戲,重敘經驗、描繪演員甚至導演手法都可以,重點是只能是敘述,不能抒情、說理或論證。第二個練習是從自己原本寫好的文章[4]裡選擇一個論點,去寫一個反論證(anti-argument)去反駁自己原來的論點。每次完成,我們會朗讀自己的文字,再作即席討論。
劇評可分的兩個部分——劇與評——一個是對於戲的觀點和論點,另一個是對於寫作的技藝。後者是我此前未曾留心關注的。這次的練習,讓我自覺把焦點放在評論作為一種文本形式這個面向上面。
因不少參加者表示在寫評論時,寫描述的部分尤為無趣,才有了練習一。練習之後,我發覺並不能將「描述」當作中性的。它背後關乎寫作的距離、呈現的取捨、主次輕重的把握。若再往上提升,則更是關乎風格、風度甚至關乎作者的見地和境界。而練習二則聚焦評論的平衡與公允。對於我們極其喜愛或極其厭惡的戲,我們是否還可以寫出一篇平衡而公允的評論?當然,問題可以再後退一步,評論是不是必須要是公允的?有傾斜的評論可以嗎?情感滿載(無論積極還是負面)的評論可以嗎?純主觀的讚揚或批評可以嗎?這些問題,便不可避免地引向了關於評論本質的討論:究竟什麼是評論?評論為誰而寫?怎樣區分專業和不專業的評論?
爭論之中,來自克羅地亞的劇評人Alen提供了一個關於評論的定義,是克羅地亞戲劇學者Sanja Nikčević基於她過去十年所做的實證研究給出的。她搜集不同渠道所發佈的劇場評論文章,然後根據這些文章的共有特性,而給出了這樣的一個定義。一篇評論[5]的組成應包括:
1)演出的信息(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ion)
2)描述這個演出(description of the production)
3)對於這個演出的評定(evaluation of the production)
4)論述這個評定(elaboration of the evaluation)
這個定義一抛出,討論更加升溫。對於這個定義,我基本是難以反駁的,但在場參加者很多皆有不同見解,甚至激烈地反對。他們質疑,評論是不是只有一種寫法?而有沒有更大想像空間的評論?有沒有更具實驗性的評論文章?
甚至再進一步,劇場評論是否只可以附屬於劇場作品?無論評論是對於劇場/作品的宣傳、評價、闡釋或紀錄,評論相對劇場而言都是處於從屬的次要地位,但評論本身是否可以成為一種獨立存在的文本?評論有沒有可能和力量躍居主位?評論是否可以有更自足的位置和更大可能性的影響力,有延展到劇場作品之外去生長的生命力?
甚或,再激進一點,評論有否可能超越文本?評論可否延展成話語?評論是否只可以是成文的,有沒有可能具化成評論人的在場和表達?評論可否作為一種行為/行動?以身體形式呈現,在社會互動的空間,以溝通的形式在創作者和欣賞者之間持續展開張力?
老實說,此次討論揚起的浪頭極多,亦不斷越過我慣有的邊界。走筆至此,終究只能將問題一一陳列,而將答案留待未來。
在回程起飛之前,我在機場看著遠處的群山,心想,歐洲的山和香港的多麼不同。香港的山通常無法被完整地看見,而且高而密集,擠在一處。但這裡的山不慌不忙一樣,寬闊地延展開去,並不高,如略厚的被子那樣蓋在這座普通東歐小城的邊緣。不見太多高大木本植株,遠看山上的大抵是草,乾枯色而不是綠意盈盈的那種,灰黃灰黃,像不搶眼的土耳其地毯的色樣。飛機起飛,爬升,我的視野漸漸擴充至整片城市,建築與街道。我看見城市的紋理,看見市中心那座曾拜訪過的教堂。它安安靜靜地,懷著六百年歷史,是羅馬尼亞最高的教堂。在這兒結識的朋友說,你進去裡面的時候,教堂如此大,天花這般高,你便深深地知道自己多麼的渺小。群山的穩穩連綿和教堂的赫然矗立,將我此行學習到的,化成了最好的相。
作者簡介:愛書,愛智慧和藝術,更愛生命本身。
照片提供:梁妍
[1] 參加者很大部分來自東歐。此次工作坊原本分法語組和英語組,但因法語組人數太少,便將其參加者合併至英語組。參加者共有十四人。
[2] 林克歡(2010),《分崩離析的戲劇年代》,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3] 關於Mark Brown的觀點,可見其文章The Critic is Not an Artist,Critical Stages,2012(7)。當然,Diana Damian和Mark Brown著眼的語境不盡相同,本文暫且不展開討論。
[4] Diana一開始就建議我們在工作坊期間至少寫出一篇成文的評論。有了具體的文本在手,才便於討論。
[5] 此處「評論」的定義應該指的是演出評論,而不考慮覆蓋更大範圍(例如劇團或劇作家,或者劇場生態、美學現象等大問題)的評論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