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電影學者貝雷妮絲.雷諾(Bérénice Reynaud)在《新中國,新電影》(Nouvelles Chines. Nouveaux cinémas)的第七章討論香港,名為〈香港身不由己〉(Hong Kong ne s’appartient pas)。顧名思義,殖民地昔日被帝國統治,今日受中國霸凌,城市從來不屬於它的市民,彷彿全城都是找不到歸宿的孤魂野鬼,殖民地就是鬼域。正因如此,雷諾認為,殖民地的歷史特別適合說成一則鬼故事,例如關錦鵬 1987 年的《胭脂扣》,就讓妓女的鬼魂返回現代都會的報館刊登尋人啟事,尋找忘了她的十二少,也找遺忘歷史的我們。
顯然,《詠舞南音》和《胭脂扣》之所以神似,不只是女舞者的紅唇和旗袍、男舞者的油頭和長袍,活脫脫就是電影裡梅艷芳和張國榮的造型,而是邢亮和梅卓燕成功的將舞者們化身為過往的幽靈,然後找到了我們。
闔上美杜莎之眼
或許有人覺得,以龍華茶樓作為演出環境,那些木窗和卡座,字畫和馬賽克壁磚,五十年的歲月風華早已幫藝術家備妥了歷史感,歷史應該是最現成的題材,其實不然。事實是,場所愈是古老,歷史反倒愈是難以表現。我們都知道,時至今日,懷舊的場所幾乎都成為觀光景點,而一旦被觀光化,比方某家大屋被指定為世界遺產,它或許停止了持續的朽壞,它的樣貌卻從此固定了下來,就像博物館放在防彈玻璃罩裡的古物。時間不再對它起任何變化,於是非常弔詭,歷史場址就這樣成為最沒有歷史感的地方。在這樣一個地方跳舞,藝術家不但撿不到任何現成的便宜,他的挑戰不下於英雄歷險,因為觀光客的視線正像蛇髮女妖美杜莎之眼,會石化一切。
所以,當《詠舞南音》的觀眾入場,眼前盡是日光燈照明的茶樓陳設,茶座上的舞者們靜止著,樂師吹奏著洞簫為這幅靜止的畫面配樂,宛如《國家地理頻道》澳門特輯的片頭。忽然,一關燈,室內全黑,旅遊節目的畫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聲音藝術家龔志成混音的街市聲響,逐漸滲入這片黑暗。從這關燈的一刻起,美杜莎闔上了眼睛。好比你逛博物館逛到一半停電了,周遭的文物突然都像鬼物一般隱隱浮動,彷彿封存在器物裡的幽靈被解咒了;同樣的,混音竄出的街坊聊天聲、唱戲聲,還有窗外的車輛聲、行人的落腳聲,都像是在為茶樓裡的家具和擺設配音,日常生活的聲響被剪接為這些靜物發出的歷史回聲,彷彿附著在器皿上的幽靈被喚醒了,得到釋放。而舞蹈的身體,自然最適合表現禁錮和釋放。
在侷促之間流動
歷史的幽靈得到釋放,茶樓卻顯然不是一個可以在空中做大跳躍的地方,何況舞者還不少於十人。令人佩服的正是這裡,編舞家善用中國舞的小碎步、下盤蹲低轉身等節省空間的運動方式,硬是在侷促的座位間,擠出了流動的肢體,但令人可惜的也是這裡,如果威廉.佛塞(William Forsythe)在 2000 年的《複製平面》(One Flat Thing, reproduced)已經能夠在並排的桌子接縫、桌面上桌底下俐落的位移,我們當然會期待舞者探索出更多埋藏在狹窄的桌椅間、過道旁、意想不到的縫隙,可是沒有。編舞家並沒有能夠以細膩的肢體去部署零碎的空間,舞蹈主要還是發生在預留出來的區塊,倒是侍者的身體勞動被舞蹈化,這一手轉化得相當精彩。例如一列舞者端著托盤,踩著碎步走到一桌桌的觀眾面前,把茶杯倒扣在桌面上滑行,令人聯想用骰杯猜謎的賭術,想到這也是賭,但是跟今天電腦機台前的賭比起來,是多麼的優雅,連賭都像在跳舞。
我看舞的那天晚上有個小插曲,舞者倒扣茶杯時過分用力,把茶杯碰了一個缺口。舞者緊張,觀眾比她更緊張,生怕缺口的利邊割傷了她的手,但見她以流利的手勢完成這場杯子舞,臨危不亂,更形優雅。另一次意外,舞者就沒那麼好運了。上面提到,舞蹈的區塊以茶樓原有、相對開闊的空間為主,舞者會從室內的走道移向外側的陽台,接著場燈全暗,只剩下街燈從窗外灑進來,每一個窗格外立著一名逆光的舞者,活像被困在一格格負片裡的人,明暗對調之下,變成一抹黑影。這些鬼影在窗框裡掙扎,雙手在窗玻璃上拍打,彷彿身後的現代化都市就要吞沒她們,忽然間,玻璃匡啷一聲碎裂,一位舞者的手腕上已經流出一道血痕。
照道理,演出中的意外會破壞幻覺,然而這滴血卻流得十分藝術,因為染血的鬼最能表達強烈的慾望和怨念,好比永遠在求生和求愛的吸血鬼德古拉。當然,我們不可能為了藝術要求舞者流第二滴血。
空間的幽靈
好在我們不必噬血,區均祥和老瞽師們在昏黃的光暈中登場,一曲地水南音《客途秋恨》,緩緩唱出未能如願的慾望終成悔恨。唱詞是一個名叫繆蓮仙的軍隊參事,描述他在客途中和妓女麥秋娟萍水相逢,卻因戰禍被拆散,令他思念不已,但不知她是生是死?這麼說來,他思念的是人還是鬼呢?這一想,想念成了懸念,追憶變為哀悼。所以,當區均祥唱到繆蓮仙重溫和麥秋娟的纏綿,他唱得如泣如訴,那是戀人在回憶裡重新愛了一次;我們也聽得幾乎掉淚,我想,那是繚繞的南音把我們捲進了一條時光隧道,在時間的彼端,我們恍然大悟,過去的傷人可以去茶樓聽曲,尋求慰藉,多麼幸福。我們感覺在南音的曲調和故事裡,重新被愛了一次。然後,當曲子結束,一群舞者立刻衝出來鼓掌,直到老樂師一一走下台,舞者依然揮動著雙手,卻沒有拍出聲,真的是曲終人散,失聲的觀眾說不出的失落。接著電腦混音傳來一記重低音,舞者開始失重的舞蹈、跌跤、甚至應聲倒下,我們也從溫柔的昔日跌落荒涼的現實。
對昔日的哀悼,那一對從《胭脂扣》裡走出的男女舞者表現得很清楚,他們在歌聲中現身、相擁,在混音的重拍間跌倒、攙扶,最後分頭走向對方遺留下來的空椅,他們只能帶走對方的遺物和遺愛。不過,用失落的愛情比喻消逝的過去,早就被流行歌曲唱到爛,舞者雖然跳得不俗,畢竟不算高招。這裡,我認為編舞家對鳥籠的使用更精彩,舞者起先提著鳥籠輕輕搖晃,晃呀晃的逐漸加大擺動的弧度,腿一抬,鳥籠從胯下逼進胸前,腰一彎,又從腦勺繞到後背。鳥籠變成揮之不去的負荷。翻開澳門旅遊指南,說是過去的龍華茶樓窗邊高掛著鳥籠,鳥叫聲像一道音牆隔絕了街市的喧囂,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禽流感肆虐,使得此景不再;那揹在身後的鳥籠,應該就是被疫病滅絕的回憶場景,在人身上留下的殘跡。
換句話說,如果有甚麼幽靈從鳥籠中被釋放,那不是誰的幽靈,也不是鳥的幽靈,而是這座茶樓的歷史,是城市空間的記憶,是空間本身的幽靈。當我們哀悼茶樓再也聽不見南音和鳥語,我們便見證了茶樓作為一個庶民共享音樂的空間、一個人類和鳥類共處的空間,在高度開發的都市建設中加速死亡。下一刻,我們不免從哀悼轉為憂鬱,自問道:眼前還存在的一切,包括雜貨舖、小吃攤、市集、戲院、書店、學校,乃至於咖啡室和茶樓,不也正在被大肆興建的豪宅、酒店和賭場,逼向死亡?我們已經沒有日常生活,我們活在惘惘的死亡威脅之中。因此,梅卓燕一襲黑衣、兩手黑色水袖,翩翩起舞像一隻黑鳥低空飛過,帶來了死亡氣息。只可惜她的舞姿過美了些,降低了威脅感,她的段落也太短了點,死亡應該是整場演出的核心意象。
被強光照瞎的群盲
誠如貝雷妮絲.雷諾那本書裡,討論台灣電影的章節叫做〈台北身不由己〉,過去同被帝國殖民,今天同被經濟殖民,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的不只是香港,也不只是澳門。演出末尾,舞者們身著長袍、戴著墨鏡,狀似盲人,在灼亮刺眼的閃光燈前大合照。這一幕,是我們這個時代共同的倒錯,也是散落在大國邊緣、三座小島的共相:高度的光亮並沒有讓我們看得更清楚,反倒把我們照瞎成群盲,就像我們在高速發展中迷失一樣。不過,依循同樣的邏輯,我認為最好的結尾,應該是整層茶樓燈光乍亮,觀眾卻連一個舞者的人影都看不見,只看見彼此一臉茫然,心想奇怪,怎麼剛才在幽暗裡的自己,好像反而更加清醒,關於這座城市的歷史記憶,更加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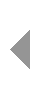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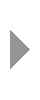



《詠舞南音》
演出團體:區均祥、梅卓燕、邢亮與澳門舞者
評論場次:2014年5月8日,晚上8時(對外綵排場次)
地點:龍華茶樓
作者簡介:現為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講師、自由撰稿人及譯者。
照片提供: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