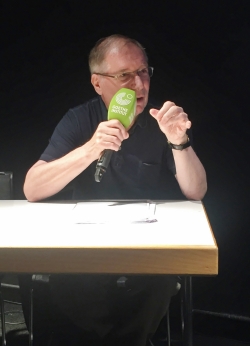2018年4月
按照一般的學科分類,表演藝術和人類學是分屬不同領域,然而,兩者都以「表演」作為研究的對象。表演藝術專注於主題與技巧在美學上的意義和價值,人類學則分析表演活動的社會影響和作用。表演研究是脫胎自表演藝術與人類學的合作,當中人類學為表演研究提供了跨文化分析的視角去比較不同地方的表演文化,也提供大量的術語和理論模型,去把作為「藝術」的表演看成是「文化」的以及「社會過程」的一部分。把人類學引進表演藝術,有助表演藝術重新自我理解,也激發對新的表演理念和表演技法的探尋。
六、七十年代這種交流和借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在反戰運動、民權運動、青年反文化運動的衝擊底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都感到要更敏銳地回應動盪的政治社會環境。人類學家不滿足於理論範式的僵化,專注於解釋靜態的社會,忽略關於社會動力。同時間,表演藝術界也感到以舞台表演為重心的戲劇藝術研究,無法回答劇場與社會之間應如何互動的問題。劇場的前衛派運動透過種種實驗性劇場,不斷探索新的表演模式,也提供了平台讓人類學與劇場互相靠近。
范金納普(A. van Gennep)和端納(Victor Turner)的研究,不但有助於戲劇藝術重新尋找其與禮儀行為的相通之處,也為諸如亞陶(Artraud)(殘酷劇場)、波瓦(Boal)(被壓迫者劇場)、葛羅托夫斯基(Grotowski)(貧窮劇場)、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環境劇場)等新戲劇實踐提供更為充分的理論說明。他們不單指出儀式行為有著戲劇性發展的結構,也說明儀式是人生階段身分轉化的機制,以及社會如何排演及解決其衝突,以及所依據的程序和規矩。
不過,對戲劇工作者最有啟發性的,莫如端納分析儀式時對「閾限」/「臨界」(liminality)概念與及「自發共同感」(communitas)的闡述。「臨界」是指「身分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當中一種過渡和不確定的狀態,一切習俗和律法的規定被暫時懸置,參與者一無所有,但亦充滿可能性。這種狀態可以衍生出現令人亢奮的「自發共同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參與者如獲新生。
對於前衛劇場工作者來說,傳統戲劇無論從美學理論的前提,以至劇場的空間配置、表演活動的安排,都是一種保守的權力機器,把表演者和觀眾囚禁在分隔的狀態。戲劇只能製造幻覺,安撫傷痛,實質上延續著觀眾的被動性和無力感。然而,透過把劇場和表演重新設想為一種儀式,一種達致「臨界」狀態的活動,劇場就有了新的意義。他們要重新定義「劇場經驗」,不滿足於讓劇場只能成為觀眾「安全地」宣洩情感的地方,而是要進一步使「劇場經驗」成為喚發不安,挑起質疑和批判能力,觸及生命深處的經驗。
除此以外,人類學家的跨文化表演研究,既使他們可以向非西方社會的表演活動借鑑,從而突破傳統西方戲劇的框框,也可讓他們重新追索戲劇未被貴族和資產階級馴化之前的西方戲劇傳統,回復那種有機的社群生活,以便重新理解劇場和表演的意義。他們也堅信,由於劇場保存了人與人的直接互動,不像影視傳播等高度地受擬象物及符號消費主義所支配,所以仍然是一個有潛力去抗衡大眾文化的空間。通過表演形式的改革,劇場的表演可以激發出「自發共同感」,復修被日常生活愚鈍化的主體性。按照這種新的烏托邦構想,劇場的改革運動有了新的方向,不單令劇場更能融入社會,甚至是改革社會的一種力量。
當然,六、七十年代的劇場藝術改革,也是藝術現代主義自身要求在形式上追求突破的產物。德國藝術評論家伯格(Peter Bürger)把二十世紀的前衛藝術分為兩期,一戰前後的立體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共同構成了第一次前衛運動,在劇場上出現了荒誕劇,使得文學性劇場無以為繼。二戰後的六十年代,爆發了第二次前衛運動,雷曼(Hans-Thies Lehmann)所謂的「後戲劇」正式登場,戲劇文本的中心地位,連同反映現實的「寫實主義」教條,都一一被正式拋棄。
「後戲劇」的出現,一方面固然是表演研究中人類學範式的某種實現,劇場表演從西方傳統戲劇美學的主宰底下解放出來,但也同時弔詭地使得前衛運動的那種劇場烏托邦構想漸漸落空。因為當日常生活的表演性、劇場性被廣泛地發掘,劇場與劇場外的世界,界限也愈來愈含糊。無疑地,前衛運動所追求的藝術與生活重新結合是慢慢實現了,劇場內的表演藝術,與可以發生在任何時地的行為藝術之間,界限也日益無法辨認。可是, 隨著表演體驗的日趨個人化,「自發的共同感」也逐漸變得遙不可及。
因為,「後戲劇」趨勢的問題,不在於我們區分表演類型有困難,而是在於當「戲劇」走向終結,戲劇所濃縮的歷史因果關係也就不再重要,生命的重大體驗可以純粹以一兩個場景姿勢就表達了。劇場之外,給戲劇化的醜聞卻日復一日地侵蝕人們的感知能力,使其麻木。歷史進程的時間和個人主觀經驗的時間擴大了分離,神聖與驚嘆不是不再存在,而是消失在混沌和收縮了的宇宙。
但事實上,謝克納和端納的人類學模型是忠於戲劇傳統的。他們所描劃的儀式有著非常清晰的戲劇結構,既有開始,也有終結,這種戲劇結構也給他們用來掌握社會的衝突和動力。端納說的「社會戲劇」(social drama)的模式,就是由「社會規範—危機—和解—再整合」等幾個「情節」所組成,與傳統戲劇的表演序列互相呼應。他也認為,社會戲劇的方式見證著社會成員之間形成關聯和團結。因為只有團結的框架存在,社會內的矛盾動力才會匯聚成衝突,成為表演的主題。也就是說,「戲劇性」原是一種方式,讓我們用說故事的方法去思考社會大方向,整理歷史事物的因果關係,找出改變命運的途徑。戲劇性的想像空間萎縮,或者把戲劇平庸化為大眾娛樂的通俗劇,反映著社會開始失去能力,去把會動搖其基本原則的威脅「戲劇化」,「後戲劇」劇場的衍生,難道不正是證明了這種能力的衰退?
當然,「後戲劇」劇場的出現,並沒否定表演研究所認定的事實,亦即日常生活充滿著劇場性質。「後戲劇」劇場的冒起也不代表劇場藝術走下坡,相反地,劇場藝術是非常快速地普及和變得多姿多彩,日常生活充滿劇場性也廣泛地變成了常識,大眾文化亦正快速地給予這些具劇場趣味的生活給予戲劇的編碼。無論是劇場藝術還是大眾文化,今日都共同構成了我們的「奇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真正要問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與自己是當中一部分的這個「奇觀社會」打交道?劇場上正在「消失中」的「戲劇」想像能力,作為一種既是太熟習,也是太陌生的傳統,究竟又意味著甚麼?——這也許是當下表演研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吧。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